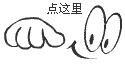一個朋友的母親去世了,他哭得暈了過去,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我們吊唁完老太太,趕忙到醫院去看他。
見到他時,他半躺在病床上吊點滴,眼睛紅紅的。來不及寒暄,他就開始跟我們數落起他老婆來:“哎呀,她要急死我了!我躺在這里算個什麼事兒啊!家里天都塌了!我,我得回家忙大事兒去啊!”說完,他竟絕望地啞著嗓子號啕大哭起來。她老婆也跟著哭,用力按著他的手,跟我們說:“家里的事兒,有人忙。人家醫生囑咐過了,必須得輸完了這瓶液再走——你們說,老太太要是九泉有知,肯定也願意叫她兒子先在醫院把身體治好了吧?你們快勸勸他吧,他這麼鬧,老太太怎麼能走得安心呀……”
我們七嘴八舌地勸慰了他一番,無非盡是些“節哀順變”之類的話。他稍稍平靜了些,開始絮絮地跟我們說起了往事。
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我可憐的母親犯了一個錯誤——一個她用三十四年的眼淚都洗不掉的錯誤啊。
我父親死得早,母親苦巴巴地拉扯著我和我姐姐過日子。三十四年前的7月28日淩晨,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我母親僥幸從坍塌的平房中逃了出來,我和我姐姐卻被壓在了廢墟下面——我在東屋,我姐姐在西屋。我母親瘋狂地喊著我們姐弟倆的名字,用兩隻手扒了東頭兒扒西頭兒,十個指甲蓋都扒飛了。
天蒙蒙亮的時候,我三舅扛著一把鍬從劉火新莊趕了過來。我母親一見到我三舅,哇地大哭起來,說:“倆孩子都不見動靜了呀……”我三舅為難地看看東頭兒,又看看西頭兒,問我母親:“快說,先扒哪頭兒?”我母親說:“你扒東頭兒,我扒西頭兒。”三舅說:“不行!咱倆得一塊兒上手,盡著一頭兒扒!要不倆孩子都得耽誤嘍。”我母親哭著說:“那咱就先扒東頭兒吧……”就這樣,我被先扒了出來。等他們再回頭去扒我姐姐的時候,已經晚了……
我差不多聽了上萬遍這樣的話,“你說我咋就昏了頭,聽信了你三舅的話呢!”我母親堅持認為,如果她和我三舅各扒一頭,我們姐弟倆就都可以活命。但是,我姐姐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母親隨身揣著我姐姐的照片,遇上高興的事兒、不高興的事兒,都要掏出照片來跟我姐姐說話。
在我姐姐五周年忌日那天,我家剛從簡易房搬進新房。我母親帶著我,到十字路口給我姐姐燒紙。她哭著告訴我姐姐說:“閨女,咱搬進新房了。這回呀,你住東屋,讓你弟弟住西屋——閨女呀,你願意不?”那次的大哭,使我母親本已哭壞的眼睛更加惡化,一點兒都看不見了。
我可憐的母親,一直活在她認準的自己犯下的那個錯誤的陰影里。我發現,她後來甚至不能聽到“東屋西屋”、“東頭兒西頭兒”這樣的詞語,一聽到,就犯病似的渾身哆嗦,眼里的淚怎麼都止不住。最近這幾年,她腦子有些糊塗了,常把我當成早已死去的三舅,用哀求的口氣跟我說:“三兒啊,你扒東頭兒,我扒西頭兒,倆孩子都能保住!”
我總覺得,我的身上有兩條命——我的命和我姐姐的命。三十四年前,我母親被擺在了一個讓她撕心裂肺的選擇面前,她選擇了我,卻又長年為這選擇支付著高額的痛苦。現在,我母親走了,我對我姐姐的在天之靈說:“姐呀,姐呀,你別可怨咱媽。人活世上,最要緊的無非一顆心、兩隻眼。咱媽把一顆心剜給了我,把兩隻眼剜給了你,她自己什麼都沒有了呀!姐呀,在那邊替我照顧好咱媽吧……”
所有的人都哭了。年輕的醫生擦著淚水塞給朋友一張紙條,說:“這是我的手機號。回去把家里的事兒料理好,要是感覺身體不適,就給我打電話,我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