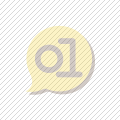01
愛情死亡之前,會有怎樣的彌留狀態?
布裡吉特·吉羅在《愛情沒那麼美好》裡,描寫了十一種。每一種,都冷硬,無情,又真實。
讀著讀著,那種壓抑感如同乾冰,忽然升騰而起,霧蒸蒸,煙濛濛,從身邊的地板罅隙滲出,從書架流下,從傢俱與傢俱的間隔中奔泄而來,包裹了你整個人。
你知道,你仍然活著,可是你感到窒息。
你想伸出手,左翻右撩,想去抓住一些什麼,但最終,你沒有伸手,也沒有呼救。
你只是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不能與無能,在你的房子裡衝撞、粹變、雜糅、揮之不去,愈來愈多。
誰沒有感受過那種平凡的絕望?
誰不曾經歷兩個人的溺水,卻又無能為力地任之沉淪?
誰不曾遭遇過窒息的爭吵,兩個人,兩種生物,封閉在各自的邏輯裡,對話只成空洞的自言自語?
這就是生活。
從PS版本,還原成真相的生活。
從懸浮於空的幻想,恍當一聲,砸到地面的硬梆梆的生活。
沒有啪啪啪,沒有法式熱吻,沒有床,沒有叫喊與呻吟,沒有你儂我儂大家儂。只有永無止息的疲憊、無聊、瑣碎和互不相讓。
曾幾何時,我們從對方的藥丸,演變成了對方的傷口。
從對方的竹杖,演變成了對方的荊棘。
它們不龐大,甚至肉眼難尋,只是遍佈於身,蝨子一般,咬噬著兩個人的生命。
只有性,還在支撐。
更多性,也不再支撐。
02
從小說裡走出來,看到你我的生活。
不同的時空,相似的平庸,同樣的羞恥、苟且、千瘡百孔。
一個結婚多年的女友告訴我:早已沒有了床事,當年以為對方的呼吸,就是彼此春藥的時期,稍縱即逝,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也不會離婚。她在這場婚姻中,呆得太久,習慣了這種模式和消耗,離了反而無所適從。只是熬著,饑渴著,任由沉沒成本愈來愈大,直至她無法負擔。
一個多年前的表親,女人,精明強幹,活得氣派周全,做生意,蓋新樓,兒女雙全,說起持家的本領,鄰里無不誇讚。
忽然有一天,出了家。
我們乘車去一個遙遠的寺院看她。並不好找,出了城,上國道,入土路,幾經周折,才看到那座廟宇。
她穿著灰色僧衣,坐在我面前,一掃從前肅靜的模樣,像一團枯枝,彎下去,蜷下去。
問她好不好,只是阿彌佗佛,並不答話,自稱青絲落,紅塵忘,六根除。
從此三生煙火,四面來風,五穀雜糧,都和她沒有關係。
但回來以後,聽同車的人說,本來也是傲氣的人,後來老公出軌,又不覺得有錯,追問起來,竟拳頭相向,最關鍵的是,他不再觸碰她。
她丈夫,一個小地方的生意人,卻像個隱居山林的俠客,待人接物的方式始終有著不切實際的豪爽,但凡誰有麻煩,不問輕重,也不問親疏,調兵遣將、兩肋插刀。他憑著那一套江湖義氣,開拓著這個世界,也開拓著各種女人。
在他的概念裡,性是性,責任是責任,情人是情人,妻子是妻子。他不以為罪,甚至隱隱有自豪。
她鬧過,哭過,歇斯底里過,但面對一個無知無覺的人,千方百計,最終都變成無計可施。她從憤怒,到委屈,到無助,到終於絕望,心一點點灰了,也一點點荒了。
她曾經想過,忍吧。大家都在這樣的灰心裡,一天天地熬。
她為什麼不可以。
但終於屈辱,她說:“不,我要出家。”
她的萬念俱灰,只有萬念皆空,方能來救贖。她什麼都沒帶,一個人,離開家鄉。多年以後,家人得到音訊,她在一個小廟裡,伴著青燈古佛,度過餘生。
同車的人依然在敘述。
在他看來,這就是鄉村浮世繪,沒什麼大驚小怪。出家、出世、出人命,都是尋常事。只是之於我,這般重錘擊鼓的話,聽得還是驚心。
我能說什麼?
我只是想到一句話: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這當然難以做到。
她能做到的,也不過是:“一入空門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03
女友的苦悶,遠親的寂滅,連同我自己的欲語還休,都不過是滾滾紅塵中,避不開的難,繞不開的結。
在一場歡愛的餘興裡,青春的激烈和衝突剔盡,它留下的,只是那種難以忽略的觸目的乏味,令我們難以言說。
是誰說,慧極必夭。
是誰說,情深不壽。
盛情不久長,激情太短暫。
仿佛一轉眼,多巴胺與內啡肽就已退場。肌膚上的快感,身體內的潮汐,方生方死,乍開乍謝。
一切都是有限的。
這個限度,科學曾有過調查和統計,最短是四個月,最長不過一年半。
而在這之後的餘生,我們又該如何相互扶持著,共同度過?
在古時,我們靠倫理道德。
在今天,我們靠門當戶對的身份,旗鼓相當的人品,棋逢對手的智識,異曲同工的價值觀。
04
這是日本電視上的一段街頭採訪。
記者問行人:“如果現在去天國,你打算帶什麼去?”
當問到一位老人時,老人回答:“我會帶上一朵玫瑰花。”
記者問:“為什麼?”
老人平靜地回答:“我好久沒見我的妻子了。”
2010年,史鐵生先生逝世,次年在北京,我見到了陳希米。一個溫慈的女人,腿也不方便。
那時正是先生去世不久,她剛回出版社上班,面容平和,沒有悲戚之色,與我們交談一二,分了手。我對她印象極佳。
後來,她的《讓死活下去》出版,在其中,我讀到這樣的句子:
我只想能跟你在一起安安靜靜地說話,聽你掏心掏肺,也跟你袒露一切。那才是人最好的生活。
那時候,我忽然靈光乍現,或許,真正的愛,不是海水與火焰的激情,而是天長地久的願望;不是狂熱、銷魂、欲罷不能,而是持續一生的虔誠、敬重與珍惜。
而茨維塔耶娃和里爾克,這一對從未謀面的佳偶,窮極一生,都在為對方寫情詩。
茨維塔耶娃的情人馬克西米里安•瓦洛申這樣描述她,“當您愛一個人的時候,您總是想讓他離開,以便去思念他”。
以上所有範例中的愛情,都與啪啪啪無關。
但是,他們都在愛。
或許,在愛的路途上,除了身體,還有另一條分叉路,引向一個叫靈魂的地方。
05
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的人裡,講到最完善的人,其對生活最重要的取向,是潛能的充分發揮。
在他們看來,性和愛是統一的。
純粹的性,只是一種生理需要。在不能夠整合的情況下,寧肯選擇高級需要,而不是低級需要。
這是《動機與人格》中的句子:
在自我實現者身上,性高潮比在普通人更為重要,同時又不如在普通人那麼重要。
性體驗是一種深刻、幾乎是神秘的體驗。但如果性欲沒有得到滿足,性的匱乏也容易為這些人所忍受。
這並不是一個悖論或矛盾。它是由動力心理學理論引發出來的。在更高需要層次上的愛,使那些低級需要,及其挫折和滿足,變得較不重要,偏離生活中心,也更容易被忽略。
但是,一旦這些低級需要獲得了滿足,更高需要層次上的愛,使人們更加專心致志地享受這些需要。
一個我所認識的長者,曾經和我聊過類似的話題。
她是心智通透的人。也只有夠透徹,夠無畏,夠平和,才能將這種毛茸茸、濕漉漉的話,說得無比端莊。
從年以前,她患上某種癌症。為了保命,切除了某些生殖部位,以至於不能再享受一個女人的歡娛。
她被這個一刀兩斷的儀式驚醒,一下子意識到,她已經是個“宣佈作廢”的人了。
春夜裡,她躺在病床上,大月光斜進來,在地板上呈菱形移動。她清晰地,感知到臟器下滑,從胸腔,滑到胸腔。而靈魂深處,也有某些東西正在坍塌。
一切都像收兵的號角。
但是,她並沒有走向她的末路。
無法以色悅人,以心悅人,以智悅人,以品性悅人,一樣很撩人。
她接受了開放式婚姻。除了性,她與丈夫的擁抱、親吻、交心、人格的共鳴、靈魂的映照,一直在繼續。
如果說,性是最濃烈的本能。那麼,愛就是最性感的文明。
而婚姻,除了本能的不請自來,更需要文明的登堂入室。因為,只有接納了後者,即使雙方走到“山重水複”,也會迎來“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