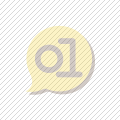當我跌跌撞撞從賓館跑出來的時候,看到了一臉無辜的張睿,不由分說,我一個巴掌狠狠的抽了過去,他也沒有閃躲。
我問,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在短暫奔跑的過程中,我就在一直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我不願意想,我更願意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假像,剛才都是一場夢。
兒時的夢,多少次,我站在偌大的庭院裡,周邊的香椿樹罩下一大片的陰涼,還有匍匐在腳邊的懶貓,突然我發瘋一樣覺得,斑駁的樹杆開始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泡著大蒜的水缸會變的血紅,披頭散髮的魑魅鑽出來,青面獠牙,雪白的牆壁仿佛有了生命,全部在顫動,在發生瘮人的笑,寒意從毛孔裡鑽出來,濕了後背,我尖叫著醒來,看到母親在身邊,一切就心安。
現在,我依然這樣,在大學裡,我害怕一個人的教室、圖書館,僻靜小路,我喜歡人多的地方,但前提是大家都保持著自己的姿勢,人多是一種場景,一種氛圍,而不是人潮洶湧,人際肆意的嚷嚷。
那樣我會感到煩,十二歲我依然幫媽媽纏毛線,把穿舊的毛衣拆開,混合上新的毛線,再次鉤織,我在這個過程中常會被斷裂的線頭接成的疙瘩攪得心煩意亂,乾脆,趁母親轉移注意力的時候,岔開,用力,把他們統統分成更小的短頭。當然,母親會狠狠的訓斥我一頓。
這種偏執略顯神經質的做法一直到遇到他,我才稍稍收斂。
只要坐在他身邊,看著他,他有種寧靜的力量,讓我心安,這是我不曾有過的,安全而又舒適。陽光的午後,他來到圖書館,光芒濺起的塵埃在他身後形成一圈金色的圈圈,他看起來真的像個神,我更願意把他噁心的比喻成天使,守護我的天使。
他也委屈的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辛辛他愛你愛的那麼辛苦,委屈你一夜又有什麼關係呢?!
看他說的風輕雲淡,我則撕心裂肺。這就是不愛,不愛我,當初又來騷擾我幹什麼?他不是女人,他怎麼會理解,第一次,初夜對於女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交付與遵從,不僅僅是身體的給予,更重要的是一生的寄託。
早上五點,窗外一片蕭瑟冷清,我睜開眼,看著眼前這個光著膀子,在我身邊的男人時,我猶豫下,輕輕喊,張睿。可蒙著被子露出那張臉時,竟是辛辛。你可以想像我心中巨大的落差,就如掉進了萬年的冰窟,全身迅速結冰,我穿著黑色的線褲就跑了出來,那個主廳的服務員看著我,滿臉的不解。
馬路上是下後夜班的藍領和白領們,全都頂著一個個黑眼圈,面無表情麻木的從我身邊穿梭而過,沒有人會停下來感知我的悲哀。張睿這樣做,還不如直接拿一把刀直接砍掉我的頭顱,與其這樣慢慢的折磨,不如這樣死的痛快,大義凜然。和愛的人在一起那是幸福,和不愛的人在一起那是什麼?比痛苦更嚴重,更恐怖,痛不欲生死不瞑目。
辛辛今年剛滿十八歲,昨天是他的生日party,他是張睿的鐵哥們,自然也就是我的朋友。我喜靜,對於這種場合我一向是諱莫如深,不願過多的接觸,那種喧囂,那種熱鬧是不屬於我的。我的世界只有火車急速而過,轟隆隆碾壓在枕木上的聲音,只有叛逆的小時候乘坐一輛車,在不知名的網站,隨著一大幫的人流而下,在陌生的近村開始旅行,開始蹲坐在一塊年久的青花石板上呆坐上幾個小時,然後再按圖索驥,回家去,當然,避免不了一場的挨駡,不過,我早已經習慣了。
習慣是個好東西,就像我習慣了對張睿的言聽計從。只是因為愛,以前的他那裡去了?我看著眼前這個男子,想著三天前,在後山的土地廟裡,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心口,一臉鄭重的說,你就是今生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面前的土塑的土地神爺爺眼睛怎麼亮晶晶的,難道也是在感動了嗎?我現在才知道,神仙也會有所謂的鱷魚眼淚,而他這一切都是TM的作秀,簡直可以去拍攝瓊瑤戲中的男主角了。
他哀求般的說,你這麼漂亮,給我去撐個場子。我點了點頭,甚至沒有考慮我一個女孩處在一大幫男子中,小綿羊和大批餓狼就是那樣的形式,誰能做保證不會發生點什麼呢。但我真的是鬼迷心竅,哪會考慮這些,精心打扮一番,就隨他而去。
在聚會上,大家都很high,我當然也不例外,我懂得,這是他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我放下了所有的矜持和自尊。當一杯杯的酒入喉後,我神智犯渾,但是沒事兒,不是他就在我身邊坐著的嗎,他眼睛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溫暖,在他身邊,就是我整個春天啊,鳥語花香,香氣嫋嫋。
我喝高了,喝高以後呢?誰記得呢?只是記得天亮後,身邊成了辛辛,不是張睿,這才是我所痛心的。這難道就是我所愛的人嗎?!
我打通張睿的電話,他非常不耐煩的說,幹什麼,頭還痛呢。
開始罵,開始用最惡毒的語言詛咒,他終於清醒了,然後又溫柔的說,不會吧,絕對不是我做的,肯定是你自己走錯門了,現在還在這裡埋怨我。然後,斷了線。後來,他趕了過來,開頭的一幕就是,後來,他走了,他走的時候,特別男人,連頭也不回。
辛辛追了出來,對我道清了事情的原委。辛辛說,他愛我,但是總覺得我跟個冰山美人似地,於是讓張睿把我追到手然後趁自己18歲時,把我當做成人禮送給他,也算是了卻了他的遺憾。終於,哥們兒情節嚴重的他竟然照辦了……
感謝辛辛的誠實,我把所有的戾氣都抱怨到他身上,左臉右臉,十條火辣辣的指頭印。
我問,為什麼不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