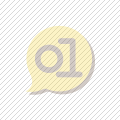我依然找不到我們分開的理由。
有時候,愛走,和愛來一樣沒有理由。
事實上,我們分開了。大三那年,我們分手了。
你不要以為我是為了故事情節在瞎掰,試問誰捨得,誰有勇氣將自己用生命去愛的歲月當故事一樣講得跌宕起伏?
寫到這裡,我想哭來著,但是已經沒了淚水。我說過了,沒了愛的激情,就好比60歲的老女人乾癟的乳房,再用力也哺育不了孩子了。
我的淚,早在1999年的秋天,流幹了。
1998年12月,小均的生日,我去了廣州。
那時,我給一些雜誌寫稿的錢已經可以支付學費了。
我給小均買了一大包禮物,從衣服到襪子,從剃鬚刀到花露水,禮物雜亂瑣碎,小均卻高興得言語哽咽。他知道,這細密的心思,都是愛。
那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的幾個同學一起去吃飯,席間,我發現他和他的某個女同學互相擠兌,精彩對白迭現,這個小均,是我所沒見過的。我所見到的小均是溫和的細緻的深情的,這個講著笑話瞎貧的男孩,我很陌生。
那個女生是那種很爽朗的很有才華的女孩,他們居然在飯桌上對起詩來。天可憐見,我早已經把背過的
唐詩宋詞拋到腦後,想當年我是多麼博學,而李小均,他是什麼時候開始對文學感興趣的?
他們背到陸游和唐婉的《釵頭鳳》時,我黑著臉站起來就走了,拋下一桌子人瞠目結舌。
其實有一些東西,是我忽略掉的。
我愛李小均,愛到骨髓裡,我再不看其他異性一眼,也不允許他看別人一眼。
我說小均,你是我的世界,我只有你,我沒有別的,我不許你離開我,除非我死。
我偏執多疑,任性,佔有欲望強烈。
我經常在半夜給小均打電話,只要他的同學說他不在,我就整夜睡不著,第二天我就會揪著他問個不休。
我離開飯局的那天晚上,一個人跑到廣州站去等車,依然坐在那個高高的臺階邊,頭靠著欄杆。
我想把這四年理出個頭緒來,我為了李小均丟失了自己。我分分厘厘地要,他分分厘厘地給,要到最後我發現,他給的不是全部,而我以為這是全部。
我敏感而憂鬱,歇斯底里在骨子深處某個地方潛藏。
12月的廣州,白天驕陽似火,夜裡卻也涼得刺骨。
我昏昏沉沉,在廣州站睡去。半夜裡,我被人抱起來,驚醒,一個巴掌摔過去,卻發現是小均。他就那麼抱著我,任由我摔打蹬彈,我口無遮攔地罵他,我在他白皙的手腕上咬出一排排牙印。他就是不出聲,抱著我走得飛快。
他將我徑直抱進流花站邊的一個賓館的房間,扔在床上。轉過頭去卻是一聲悶悶的哭聲。
長長的寂靜無聲,讓我覺得胸悶。
我撲過去伏在他的背上,我喃喃地說:小均,我愛你。
他緩緩地轉過身來,擁抱我,親吻我的眼睛、我蒼白的臉頰和嘴唇。
然後,他要我。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我們約定要將這一天留到婚禮那天,然而我們沒有。
一切都自然而然,我們生澀,戰慄,恐懼,興奮,瘋狂。
一個晚上我們一次又一次,流著血流著淚流著汗。
天亮的時候,小均牽著我的手,從賓館服務員身邊悄悄溜下樓,我們偷走了那條床單,那上面有我處子的純淨血紅。
1999年的夏天,我去了廣州,準備為實習找單位,我開始預備起一年後和小均雙宿雙飛的生活。
自那夜後,我們再沒有越雷池一步,我們還可笑地約定,將第二次留到新婚之夜。我們在說這話時,臉上有神聖的表情,當時似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