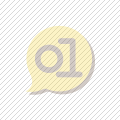我這一生活得奇奇怪怪。不知道為什麼,所有的好事總在最後一刻雞飛蛋打,而所有的壞事總是在最後一刻說出現就出現,沒有任何徵兆。而且,所有的沒有結果的事情總有一個很美好的開頭;一開始磕磕碰碰,一波三折的事情最後卻有可能出人意料成功。
我的前夫是計程車司機,我原來單位在環衛局,工作不稱心,所以我一直混混病假什麼的,沒有正經上過班。有時候,也教鋼琴。我從小就操練鋼琴,本來父母也沒有指望我在這方面有大的發展,只是愉悅自己而已,誰知卻成了我謀生的飯碗。
我娘家在建國西路,是老洋房,我從小最喜歡在高高的屋頂下在灑滿陽光的窗前彈琴。但是我弟弟後來從外地回來,就住了我原來的房子。我也不好說什麼,我媽說,你們有婆家的都到婆家去住,我這裡要照顧沒有戶口的。所以我也忍了,算了。
可是等我離婚以後卻發現建國西路的房子現在已經分戶,而我以前那間房子的戶主已經是我弟了,人事全都換了。他們不歡迎我住回來,即使是我離婚以後。這一點,很傷我的心。
所以我離婚後還是住我結婚時的房子,那房子在我婆婆的名下,因為是他兒子的錯處,又考慮到我的現實處境,所以我婆婆對我約法三章:我如果不嫁,我可以一直住下去,如果我再嫁,房子就收回。
我婆婆的心情也很複雜,一方面希望我再嫁,她可以收回房子。一方面其實暗暗希望我不嫁,這樣他的孫子還可以到奶奶家走動走動。以前或許還有讓我重婚的意思,可是他兒子現在已經再婚。
我婆婆也許並不喜歡我,可是更不喜歡繼任妻子。我有文化,至少還能勝任教好她孫子的責任。可是我媽接走了樺樺,我媽挺喜歡樺樺的,我兒子叫樺樺,白樺樹的白樺。我從小喜歡俄羅斯文學,白樺樹是俄羅斯文學常見的一個意境。想想看,直溜溜的一排排白樺樹,遠遠望去,說不盡的純潔與挺拔,給人一種多美多詩意的想像啊。所以,我現在住在宜山路的一房一廳,一人獨住。
我婆婆包括外人都不理解我和家基的離婚,人家都說我們是天仙配。可是我們合不來。家基文化差,再說整天在外開車,說話“切口”很多,我看不慣。他則聽不慣我鋼琴的練習聲。
他半夜三更回來,倒頭就睡。等天亮了,家家戶戶開門上班的時候,他開始醒了,就硬要我與他過夫妻生活。當時我住在婆家,其他叔伯妯娌紛紛開門推車上班,日高三尺,我們卻在床上呻吟喘息。
我甚至可以想像他們在背後竊笑的聲音。可是家基說我“想像力太豐富,夫妻間的事情,有什麼難為情?”他總說我是“大小姐脾氣。上班不肯上,飯菜不會做,妻子也做不來,還要擺大小姐架子”。
婆婆與我住一起,就隔一層牆。開門以後,我總是不敢抬頭看他母親的眼睛。樺樺出生以後,家基回家的次數越來越短,後來終於給我抓住留宿在第三者家裡的把柄。婆婆在人證物證的情況下,也無話可說。
我一個人獨住,鋼琴也教不成了,地點太偏,原來的孩子上門不方便。而周圍的環境我還沒有打開局面。於是我找了個活,在匯金商廈當營業員。不忙,而且是做一天休一天的,每月1000元左右。
我變得很憂鬱,我媽把樺樺接了過去,是想讓我方便一點,可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就更孤獨了。別人也給我介紹過人,可是我總不滿意。
在辦離婚案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律師百器,他挺同情我的,在分割財產上面幫了我很多的忙,使我拿了三萬元的補償費。當時正是生意熱的時候,我把三萬元投資做生意了,可是連本都蝕光。
我離婚一年以後,百器在靜安錦亭請我吃了一頓飯。錦亭是中國式的香豔格調:富麗堂皇到頭又折回到雅的裝飾,暗合中國人內心浮華的心意。杯盞交錯之間,百器舉起酒杯,看著我說:“金碧輝煌的感覺很好。我們再來一次筵席,好嗎?”“就是那種總要散的筵席,好嗎?”
我裝作沒有留意聽的樣子,眼睛望著那種令人心裡起霧的燈光,我聽出來他話裡面的意思。他是從一開始就制定好遊戲規則,範圍與距離都已經匡好。可我不想這樣,我是要一步步往下走的,因為我知道我要的是婚姻。
百器與妻子不和。據說是因為他妻子曾經出賣過他父親,現在又是性冷淡。我說,“我也是”。百器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誰知這一眼就看到我心裡去了。我也不去追究事情是真是假,我沒有這種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