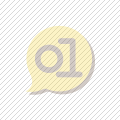男人應該是什麼樣的
我和老公子偉都是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的同學,2001年畢業後,我到了設計院,子偉到了裝潢公司搞室內設計。順理成章的,2004年秋天,我和子偉舉行了婚禮,當時我們班,像我和子偉這樣修成正果的可不多,同學們都很羨慕。
婚禮在香格里拉酒店舉行,我是南京人,父親是公安局的處長,母親是鼓樓醫院的護士。婚宴上,幾乎都讓我的親戚朋友和父母單位的同事包了。而男方那邊就冷清得多,子偉是安徽人,家在農村,他父母都沒有來。
我的父親可能喝高了,他講話的時候居然把子偉的名字也叫錯。旁邊的人竊竊私語,都說那個窮小子,高攀我們家了。
那一晚,子偉拚命喝酒,好像要把全場的喜酒都喝光。
回到我們的新婚套房,子偉忍不住吐了出來。我絕望地看著被弄髒了的婚床,想我的新婚之夜,就這樣泡湯了。我幫子偉脫掉衣服、鞋子,和衣躺在房間的地毯上。雖然我和他都不是第一次,但這樣的新婚之夜算怎麼回事。以後等我老了,回想起來,新婚的夜晚就充斥著酒氣、污穢和苦澀。
忍了很久的淚,就那樣涌了出來。
新家是兩室一廳的房子,客廳和主卧都很大,還有一間小房子,本來準備把它當客房的。子偉還沒醒的時候,我就悄悄回家,買了新的四件套,把小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把我的泰迪熊也拿過來,布置得很溫馨。我父母的家,是不能回了,當初他們就反對我和子偉結婚,現在回去,還不是自討苦吃。我就把這客房當作是我的「虛擬娘家」。
快傍晚了,子偉才醒過來回家。我躺在小床上,板著臉不理他,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膛:老婆,你聽聽,我的心都是為你跳的。我堅硬的心軟了,我是愛他的,還賭什麼氣。他把我拉回卧室,雙手環上我的腰,對著我的耳邊:說,你想要我嗎?
我的家庭教育很古板,性是雷區,從來沒有人觸及。他的問話太直白了,我的身體、我的情感都想他,可是我說不出口。子偉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身體上,仍然倔強地問:你,你需要我嗎?我的頭低低地垂在他胸前,含糊地「嗯」一聲,讓他去領悟我要還是不要。這已經是我的底線了。
子偉的呼吸開始加快,他的手指甲,毫不留情地陷進我的皮膚里。我承受著他的瘋狂,把他越抱越緊。在最後崩潰的時刻,子偉的撞擊似乎帶著怨恨:淡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根本不想要我。
如果沒有最後一句話,我們的新婚之夜也算完美無缺。我迷迷糊糊地聽著,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以後每一次,我都能感覺到子偉隱藏的憤怒。問他,子偉輕描淡寫帶過:男人嘛,不都是這樣做的嗎。但我分明感覺到不是的,他的愛做得也太狂風驟雨了,我的脖子、手臂全是隱隱約約的紅印。
他用性來感謝我嗎
我開著綠色奇瑞QQ,心情恍惚。我和子偉的關係,快讓我窒息了。
2006年三月,子偉說他媽媽的眼睛白內障,想到南京來動手術。我說白內障是小手術呀。子偉的臉就沉下來:那是我媽,你婆婆,她到南京手術有什麼錯嗎?我趕緊閉了嘴,夫妻最不需要的,就是講道理,尤其是在婆媳關係上。
婆婆來了後,我主動讓出大房間給她住,我和子偉睡小房間。子偉對我的大方很高興,其實潛意識裡,我覺得小房間是完全屬於我的,我不想讓別人碰它。我請了假,又託了媽媽在鼓樓醫院幫她找醫生、找床位,我跑上跑下,醫生還以為我是老太太的女兒,當知道我是兒媳婦,一個勁地誇她有福氣。
晚上當子偉的手試探著伸過來,我已經累得沒有力氣。子偉沒有放棄,仍堅持著不斷深入。我感覺到今天子偉的異樣,他熱切溫柔,對待我的身體就像晚清的名貴細瓷一樣寶貝。小床很窄,就像他單身宿舍的床,我縮在他寬大的懷裡,感覺戀愛時那些雲淡風清的日子又回來了。我的身體不再僵硬,在最愛的人面前漸漸柔軟、鬆弛,慾望就像林中的雲雀,忍不住想叫。子偉一把捂住我的嘴,壓抑著說:別出聲,媽媽在隔壁呢。
一年多來,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這麼和諧。我看看自己身上,也沒有了讓我辛酸的那些紅印。沒有他微妙的憤怒,只有對我無盡的憐愛。之前我的那些猜測,並不是空穴來風。子偉親了我一口,說:謝謝你對我媽這麼好,老婆。我的心頓時寒到谷底,原來他只是報恩,用溫柔的性來報答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