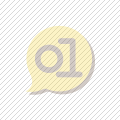我是一個有紅杏出牆經歷的女人。這種經歷刺激著我,也折磨著我,我心裡有很多的話想找人說,有很多想法想找人溝通。
可這種事能跟誰說呢?再好的朋友都不能說,這種事,只要你跟一個人說了,那麼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了。
我看到肖劍先生的這個帖子的時候,我有點動心。我想寫出來,但對方說的是真話嗎?
我給出版社打了電話。知道了肖劍的本名,又在網上搜索了一通,翻閱了他以前的作品,其《虛掩的門》、《另一種遊戲另一種規則》都是在我的朋友圈裡廣為傳閱的書籍。我相信了他,確認他是在認真地做著一件有意義的事,至少不會是故意在別人的經歷中尋找一些低級趣味。
所以,我把自己關在屋裡,面對著冷冰冰的電腦,搜尋、整理著自己記憶里的那些溫暖的情感,全面地檢視一遍自己的靈魂與肉體。
靈魂是漂泊不定的,肉體是溫潤真實的。二者可以分開嗎?
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到深圳出差。深圳有好幾個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還有一個和我同宿舍年的好朋友小蘭。大家聚會了一次,很熱鬧也很親切。我辦完公事後,小蘭非要我再住兩天玩一玩。盛情難卻,回去也沒有什麼事,就待兩天放鬆一下吧。我同意了,讓同事先回去,我就住在了小蘭的家裡。
問題出在第二天的晚上。陪我玩了兩天的小蘭那天晚上有一個活動,她先生的公司有一個晚會,要求家屬也去聯歡。小蘭要留下來陪我,我堅持要她去,我說:你都陪我兩天了,不能影響你的正事啊!我也正好休息休息。小蘭臨走時,說:那你看會兒電視,那兒有,我這裡有不少好盤,你隨便看,早點睡吧。我說:你放心去吧,還沒老就這麼婆婆媽媽的,小心你先生煩你。
小蘭兩口子打扮了一番,就去聯歡了,說要很晚才能回來。我一個人就打開了電視,看了一會節目,覺得無聊,心想還是看張光碟睡覺吧,好長時間都沒看過西方的大片了,聽聽英語也好。
我在碟架上翻了翻,上邊的一堆我都看過,翻到下邊,有幾張盤用報紙包著,也沒有封套和說明,這是什麼?難道就是黃色影碟?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些玩意。也許是人家自己錄製的什麼吧?我有些猶豫,把光碟又放了回去,可別的又實在是沒什麼看的。過了一會兒,我把那幾張光碟又拿了出來,管他呢,看看到底是什麼,要是不對路,不看就是了。
我拿了最上邊的一張放進了機,按下了。電視機畫面一亮,赫然跳出一個一絲不掛的金髮女郎,挑逗地伸著舌頭,雙手揉捏著自己一雙巨大的乳房,扭動著豐滿的屁股,私處的體毛也清晰可見。我嚇了一跳,本能地拿起電視遙控器,把電視就給關掉了。
我坐在沙發上,心嘣嘣地跳,好像剛才在畫面上脫光了衣服的是我一樣,又覺得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彆扭極了。
我喝口水,靜一靜,站了起來,馬上又意識到這是在深圳,在小蘭的家裡。這是一間布置得很溫馨的客廳,厚厚的窗帘拉著,茶几上的小檯燈灑落暖黃色的燈光,靜悄悄、懶洋洋的感覺。
我低頭看一眼我剛坐過的沙發,寬大舒適,可以把人完全陷進去。忽然,一個念頭冒了出來:小蘭是不是就坐在這裡和她先生看這些?這些光碟雖然用紙包著,放在最下面,但小蘭不可能不知道啊,她跟我說過她晚上沒事就在家看碟,把近年的好萊塢的大片都看了一遍,那麼家裡有什麼碟片她應該是很清楚的。
她也看這些?一個人看還是和先生一塊看?那麼……
我覺得自己的臉開始發燙,我怎麼想這些,怎麼回事。我重新坐到沙發里,獃獃地望著黑黑的電視屏幕,腦子裡亂七八糟的。這時我發現,我剛才只是關了電視機,機還開著,碟片還在裡邊播放著!
我伸手拿起了機的遙控器,想停止它。可剛要按下去的時候,又把手縮了回來:
那裡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猶豫著,放下了的遙控器,拿起了電視機的遙控器,打開了電視!
一陣喘氣和呻吟聲立即充滿了房間,我又嚇了一跳,趕緊把聲音往下調,一直到完全沒有了聲音!接著又小心翼翼地放出點聲音來。音量是最小的一擋,除去坐在電視機前似的我以外,屋子裡根本沒有別人,窗戶也關得嚴嚴的,可我還是覺得聲音大得刺耳。
畫面上是一對完全赤裸的男女,女的就是剛才出現的那個金髮女郎。她、她正跪在那個男人的腿中間,兩手捧著一個巨大的東西,往嘴裡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