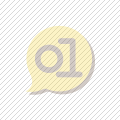性並非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與愛密不可分。愛是性的基礎,性是愛的延續。只有有了愛的滋潤,性才能開出燦爛的花朵。
20歲那年,我如願以償地嫁給一位」吃皇糧「的夫君。丈夫大我9歲,曾經結過一次婚,有一個5歲的男孩。雖說是給人家做「填房」,當「後娘」,可總算是跳出山溝進城享福了。
說實在的,結婚之初我和丈夫的性生活還是協調的。他結過婚,有經驗,又憐惜我,所以比較溫存。新婚之夜,被破處女之身的我都沒覺得疼痛,這便是例證。我在性生活方面出現障礙,完全是在我們感情方面出現危機之後。
我和丈夫的感情危機是因婆婆而起的。不知是因為年輕時就守寡有心理障礙,還是愛子心切,婆婆總不樂意丈夫與我單獨相處。晚上是沒辦法的事,如果在白天丈夫和我在一塊超過了半小時,婆婆就要尋點緣由喚他出去。
婆婆尤其看不得丈夫對我好。如果飯桌上丈夫替我夾菜,或是我洗衣服的時候他幫我晾,婆婆就會大發雷霆,繼而冷嘲熱諷,說:「少在我眼跟前演戲,八輩子沒撈著個老婆似的。」這是說她兒子的;「山旮旯里出來的裝什麼嬌小姐。」這是說我。丈夫如果稍一頂嘴,比方說一句:「娘,您這是說些啥呀!」婆婆馬上就會哭起來,哭過之後還要我不懂事的兒子唱:「花喜鵲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
丈夫怕落個不孝之名,漸漸地便不敢再對我好了。一開始他只是在婆婆跟前裝裝樣子,豈料習慣成自然,久而久之他竟弄假成真,不對我好了。感情的疏遠導致了我對性生活的冷淡,我討厭那種靈與肉的嚴重脫節,開始尋找種種理由迴避。我的冷淡和厭煩反過來又刺激和傷害了丈夫。這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我愈迴避拒絕,他愈粗暴強硬,有時候竟無視我身體的不適。夫妻反目總是沒有好話說的,丈夫也開始拿一些刻薄的語言來傷害我。比方說,我推說身體不適拒絕同房,丈夫便會說我「變嬌氣了」,言外之意是「你一個農家女有什麼好嬌氣的」。他不曉得,這正是我心中最怕疼的「痛點」――貶低和輕視我的出身。丈夫不知道,正是他這些毫無憐惜的語言漸漸冰冷了我的心。
最令我痛心的是,我小產以後才十幾天他便要求同房。我說不行,會落下病的,丈夫又拿出那些最能傷害我的話來反擊我:「怎麼這麼嬌貴?不說是肉碰肉嘛!」那次同房的結果導致了我大出血,同時在流血的當然還有我的心。
我從此便「性冷淡」了,丈失管這叫「不起性」。不管他怎樣努力,我那裡永遠像久旱的土地毫無潤澤。丈夫氣極了便叫我「木頭人」,這樣做的結果適得其反,我愈發「木頭」起來。情形愈來愈糟,以至於到後來我一看到他的「那話兒」就抑制不住地噁心,哇哇直吐。丈夫在我的眼睛裡已經蛻變為一個毫無感情的陌生人,與之同房的感覺無異於遭人強暴。
好在這種情形僅限於同房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還能和平相處。說到底,他畢竟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親,每天早出晚歸地為這個家操勞奔波,他生病了,我也心疼、著急,床前枕後地照料他。
1994年婆婆患病去世了,緊跟著我也大病了一場,是宮外孕引起的大出血,醫院下了病危通知,但我最終還是掙脫死神的糾纏活了過來。在我命懸一線的那些日子裡,丈夫的心靈和情感也經受了一次生與死的磨難。後來他告訴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才第一次清楚了我在他心目中所佔的位置。他說他真害怕我就那麼死去,如果那樣他也沒法活了。我的死裡逃生使他大喜過望,就像撿著了一件失而復得的寶貝,愛惜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我恢復的那段日子裡,丈夫對我的關懷愛護簡直到了讓我受寵若驚的地步。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丈夫視我如一件瓷器連碰都不敢碰一下。有幾次我過意不去,主動說:「你要是想,就……」丈夫總是堅決地搖頭,說:「大夫交待過,你需要好好調養。」他還說不能只圖一時痛快落下終生遺憾。人心都是肉長的,丈夫那些充滿溫情的話語猶如縷縷春風盪過我冰封的心海,我感覺那些冰正在一點點融化,裸露出來的心房開始變得柔軟、敏感,一經溫情的語語便會產生一種麻酥酥的癢感,那真是一種美妙的感覺呢。
我與丈夫真正的水乳交融是在一年以後。那是婆婆的忌日。說起婆婆坎坷的一生丈夫非常傷心,他說他母親天性並不壞,只是在生活的艱辛和重壓下有點兒心理問題。他給我講了許多有關他母親的事情,並要我別記恨並且原諒老人。我說:「怎麼會呢?怎麼說她都是你的媽媽,我能理解她。」
男人的眼淚是最能讓女人心軟的東西。望著傷心的丈夫,我感到了一種觸動心尖尖的痛。一種濃濃的愛憐充溢著我的心房,於是我產生了一種要用愛去溫暖丈夫的衝動……
那一夜,是我性的復活,也是我和丈夫愛的重生。在親情和愛意的潤澤下,一切都那麼自然,那麼合理,彷彿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作為一個女人,我想對天下的男人們進一言:請用心去愛你的妻子吧!愛妻如播種,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穫。當你抱怨自己妻子性冷淡或不夠溫存時,你是否也應當檢查一下你自己?有了愛的滋潤,性才能開出最美麗的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