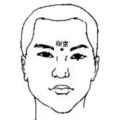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慾方面失寵。
張玉鳳與江青的合影照。(網路資料圖片) 現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思維屬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理性起著極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並非純理性的,人們同時還受情感、慾望、意志、直覺、理想、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因素的影響,這些不自覺的、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現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1]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面,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慾、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慾、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範圍和程度內,人的情慾和性慾對社會歷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是毫無疑問的。由於人的情感和性慾,產生了血親和婚姻等重要的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端的政治領袖的影響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慾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后妃造成後宮干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此類實例不勝枚舉。 從這個角度去看,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雖然毛有時會批評她,但總體來看,毛對江青的行動是相當放縱的。為何如此?是因為她受到毛的寵愛嗎?事實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慾方面失寵。 1.江青為何在“文革”中能橫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歲時,雖然風韻猶存,但她與毛在中南海豐澤園中已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這當然與毛澤東一貫在婚姻上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也與江青的婦女病不無關聯。那時江青得了嚴重的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而不得不去蘇聯治療。面對性慾極為旺盛的毛澤東,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關係方面對她的依戀。毛澤東礙於其“領袖”形象而不便離婚,但又想滿足婚外性慾,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這種默認也自然伴隨著丈夫對其名義上的妻子的某種補償。以毛氏夫婦的地位,在一切生活開支均可由國庫支付的情況下,毛若對江作金錢上的補償,並無實質性意義,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權力方面作出補償型承諾。據陳小雅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演變早在50年代初就開始了。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3]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只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諱言,予以配合。[4] 3.“文革”的發端:毛澤東對“李慧娘”一劇的反感從何而來?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自己放蕩的私生活的態度是極端虛偽的。一方面,他在性關係方面極端放縱,肆無忌憚;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盜名,維持“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因此,他對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會無端猜疑,甚至惱羞成怒,興起風波。1963年,文藝領域裡“批鬼戲”的風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聲,這場風波的發端與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慾有很大關係。 1963初,經工作人員提議,毛為了消遣,調新編崑曲歷史戲“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該戲的內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殺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復了仇。無巧不成書,在毛看此戲之前,他的一個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戀愛的男青年結婚,但是毛不肯批准,為此她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剛發生了這起不大不小的宮闈風波,偏偏安排毛觀看的是如此劇情的“李慧娘”,毛馬上下意識地認為,此戲是在影射他同樣是驕橫淫逸的私生活。據當時陪同毛澤東觀戲的李志綏回憶:當演出至賈似道攜帶眾姬妾游西湖徵逐歌舞,遊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脫口而說:“美哉少年”時,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歡去的地方。接下來演氣憤異常的賈似道殺死寵妾李慧娘。我記憶中演員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猶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賈似道報仇的情節。當時我看到毛的神態一變。毛除了偶然大發脾氣外,很少讓他的不悅流露於外。但我學會了觀察他情緒的變化——鎖緊眉頭,眉毛高挑,身體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諱了,好像以戲劇演出來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這情節使人想起了毛不準機要員和她的愛人結婚的事,她那時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馬上發動了對“李慧娘”和所有“鬼戲”的批判。一方面,他讓江青找上海的柯慶施在《文匯報》發表罕見的長達1萬3千多字的文章,題目是“駁”有鬼無害“論”。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戲‘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還正式發出檔,指責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要求全國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題材。[14]就這樣,因毛偶然看戲時毫無道理地懷疑該戲“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釀成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導火索,還為後來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提供了從“影射史學”入手進行上層政治鬥爭的範例。 5.江青奉命打擊葉劍英,毛澤東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安排入學、參軍。這股歪風邪氣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一個焦點。1974年初,毛髮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原本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裡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系工農兵學員鍾志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5]當時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有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既能贏得民心,又可在軍內擴充勢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對軍隊大權重新洗牌。面對這樣的壓力,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了關於自己的“嚴重錯誤”的“檢討”。 但是,在“走後門”問題上,毛澤東卻出面幫葉劍英的忙,妨礙了江青等人打擊葉劍英、插手軍隊事務的盤算。毛在2月15日給葉的覆信中說:“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26] 毛的說法顯然又是強詞奪理,故意曲解。江青、遲群所批判的是“走後門”這種方式,並沒有給“前門”或“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開後門”之風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據毛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27]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得不“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與這些“女友”之間有約定的“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歷史系的范達人回憶:“1973年,北大歷史系來了3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3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准她們在系裡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人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范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歷史系學習。”[28]據范回憶,這類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中共資深幹部沈容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29] 顯然,毛自己因為有“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所以他無法抓“元老派”“開後門”的把柄、藉此整倒他們。像當年為“女友”任憑林彪排擠聽命於毛的肖華、楊成武一樣,這一次是為“女友”而“放”葉劍英“一馬”。當然,在這件事上退讓,並不意味著他就不想打擊葉劍英。兩年後,他還是用不合程式的中央文件,宣布葉劍英“生病”,“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30]然而,這時候才剝奪葉劍英的軍權,為時已晚。葉已經贏得了在軍內苦心經營兩年的時間,他“病退”前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資歷尚淺的陳錫聯根本無法壓制或者忽視。毛死後不久,他生前竭盡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葉劍英勢力的手裡。毛若再世,當悔之莫及。 6.“毛辦”“負責人”:“陪睡丫頭”張玉鳳 談到毛在“文革”時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與其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據李志綏回憶,1970年毛與林彪發生摩擦,結果導致來自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失寵,此後張玉鳳正式調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過其風燭殘年的最後6年時光里,張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著毛的私人保險柜,此櫃里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材料反映了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制了黨政軍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的家人,獲得了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只有張才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複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以致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幾年前張玉鳳的一則回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提出了毛之後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了記錄。該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2]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臨終前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來更像是毛當著張的面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圖心,否則她為什麼不當面拒絕毛將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從1970年到毛去世,張對毛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稱)的範圍。張實際上扮演著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著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對她的依賴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實上從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個徒具虛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張玉鳳的真實地位,對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層政治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那時,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討論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3]由於毛晚年根本不願見江青,江青曾不斷地對張“巴結”、“獻殷勤”,即便如此,張和江的關係仍然不和諧。一方面,她們之間的“大婦”和“小妾”的爭寵奪利關係極難緩和;另一方面,張也是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了毛的一個“客人”而與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結果曾一度被毛趕出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姓女士,此人後來去香港後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4]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未在毛面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在回憶中提到,毛澤東和她(指張玉鳳)慎重地談過與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5]另據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發生嚴重衝突。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6]“文革”中毛對江青最嚴厲的批評(即批評“四人幫”)正是發生在此次衝突之後。不難猜測,張玉鳳在毛嚴厲批評江青一事上很可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容——也時常離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唐、王兩人當時比較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與江青有私人矛盾,於是就利用毛的聯絡員的身份,在極為封閉孤獨的毛面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當然,王海容同時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7]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余英時教授總結毛澤東的治國方式時,使用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比喻。此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8]確實,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慾橫流的溫柔鄉里,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為什麼無聊的事,毛與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導致心肌嚴重梗塞。當時雖然搶救了過來,但此事大大地縮短了毛的壽命。[39]毛生前雖然“妾嬪”成群,但死後屍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對於“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應和嘲諷。 [1]有關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義,可參考下列中英文著作:Richard[2]Wolin.TheSeductionofUnreason:theIntellectualRomancewithFascism:FromNietzschetoPpostmodern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4;JohnDunn.TheCunningofUnreason:MakingSsenseofPolitics,NewYork:BasicBooks,2000;JonathanBaron.RationalityandIntellig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吳寧《社會歷史中的非理性》,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夏軍《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 [3]EdgarSnow.TheLong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71.p.175. [4]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頁。 [5]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情事》。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7-338頁。 [6]黃崢,《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 [7]巴人,“毛澤東震怒--震動高層的‘竊聽事件’”,《北京日報》,2007年6月19日。 [8]最後的處理自然是對那位來自農村的姓劉的錄音員最重。據李志綏回憶,劉某被立即送去陝西勞改。據北京的知情者告知:直至“文革”結束,此人都未被“解放”。 [9]同注[3],第354-355頁。 [10]同注[3],第354-355頁。 [11]同注[3],第354-355頁。 [12]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3]同注[3],第388-389頁。 [14]梁壁輝,“駁”有鬼無害“論”,載《文匯報》1963年5月6日。 [15]“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2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6]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頁,第195-198頁。 [17]同注[3],第343頁。 [18]《反叛的御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香港:《開放》雜誌社,1997年,第29頁。 [19]丁抒,“毛澤東和他的女譯電員”,載香港:《開放》雜誌,2000年4月號。 [20]“文革”開始後,由於原來處理軍委日常事務的羅瑞卿、賀龍等人先後被打倒,經毛澤東的批准,軍委成立了一個由葉劍英、楊成武和肖華組成的“三人小組”,處理軍委日常事務。這對於林彪集團,事實上是一種制衡。 [21]同注[3],第464頁。 [22]張雲生,《毛家灣紀事:林彪秘書回憶錄》。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頁。 [23]黑雁南,《十年動亂》。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209-210頁。 [24]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672-677頁。 [25]同注[3],第508頁。 [26]《人民日報》,1974年1月18日。 [27]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頁。 [28]《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內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頁。 [29]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頁、39-40頁。 [30]沈容,《紅色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頁。該書作者在網路上發表她全書摘錄時的標題是“我所見所聞的幾位毛澤東身邊女孩”. [31]見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檔“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陳錫聯同志任職的通知”。文件說:“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當時葉劍英並未請病假,而是毛澤東“欽定”[32]同注[17],第46頁。 [33]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8月號。張玉鳳的這一回憶現在越來越被研究者們認為是真實的。 [34]同注[17].另外見郭金榮的《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第119-120頁。 [35]凌鋒,“有關張玉鳳的補遺”,載《閑話毛伯伯》。香港:《當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頁。 [36]同注[15],第185-187頁。 [37]見“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發[1976]24號,1976年12月10日。 [38]同注[3],第561頁。定”他“生病”,從而奪了他的軍權。 [39]余英時,“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載《反叛的御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第84-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