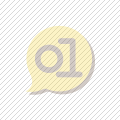她坐在化妝鏡前,穿著白色小禮服。用一條黑色大圍巾,裹著胸部,嚴嚴實實的防止走光。纏繞得恰到好處,讓我誤以為,那條圍巾是禮服的一部分。頭髮怎麼弄,她有自己的意見,不再是唯唯諾諾任人擺布的小女孩。她不喜歡梳得很死很僵的髮型,希望自然一點,再自然一點。她知道自己要什麼。
拍照的時候,她輕微轉側面龐,角度給得準確而微妙。在外人看來,也許毫無變化,但是在鏡頭裡,那一細微的一毫米,就是「好看」到「完美」的距離。攝影師為她著迷,不斷的囈語「漂亮漂亮漂亮」,就像男人情動時刻的催眠。她的狀態是一個成熟女人的狀態,享受這份恭維,此時此刻願意相信。這種相信是一種配合,你知道,在她心裡,與這份沉浸有一段距離。她知道自己該給什麼。
拍照結束,她穿回自己的衣服。一件大大的灰色毛衣,肘彎處起了毛球。頭髮全部梳起來,手背上有一塊新傷,做家常菜時不小心燙的。藍色牛仔褲,綁帶舊皮靴。她彎下腰去,鞋帶太長了,在腳腕處多繞了一圈,才系得上。
當她弄完這些,坐在你面前,又回到多年前你認識的那個女孩兒。那個時候,她乖巧的坐在我面前,穿一雙臟球鞋,像個被提問的學生,唯恐錄得不夠清楚,而全程舉著錄音筆。晚上,我們繼續電話訪問。因為信號不好,她維持著同一個姿勢,一動不動的講了一個多小時。她知道自己原來是誰,現在是誰。
她是高圓圓。這個時代最美好的女演員。有的人只是美麗,而有的人美好。有的人有魅力,有的人有人格,但是同時有人格魅力的人不多。高圓圓是其中之一。
高圓圓自述:
「我從來沒有那種自信,一個美女的自信。」
我從來沒有那種自信:從容自如,遊刃有餘。從小到大,直到現在,我的家人從來沒有誇過一句,說我長得好看。從來沒人誇過。你說我長得很美,問我是不是得到了很多優待,有很多好事發生?其實並沒有。
我只是覺得,第一,我長得還行,比一般人舒服一點兒,順眼一點兒;第二,我還是不自信。這個不自信來自於,我覺得自己知識還不夠豐富,內心不夠強大,然後我覺得我不夠放鬆,不夠有趣,不夠自我,不夠瘋狂,不夠……我從來不是一個得意的人。你看到的如今的自信,都是被建立的。
包括很久以來,我一直不好意思面對我的職業,我的身份。在我心底,我始終覺得做明星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兒。雖然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年,雖然我在享受它,但是回歸到生活里,我還是覺得挺心虛的。這種心虛大概就是,比如我愛上一個人,我忍不住會想:「對方會不會覺得我是個明星,還不如是個作家?」如果我是個作家,會令我更開心,真的。
「我把自己收了起來,像一把傘,但是期待著盡情張開。」
這種不自信從哪裡來的?我一直在問自己。也許是因為,我出生在一個保守的家庭。先有了我哥哥,很多年後再有了我。父母已經中年,他們的愛沉默寬大。他們給了我很多的自由,也給我很少的誇獎。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孩子,我一定會適當的不斷的鼓勵他,因為我知道這有多重要。
高中的時候,我拍了廣告,在學校里,突然就變得有名起來。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突然就變得很敏感,到處都是敵意。小時候我是在大院長大的,不是部隊大院,是科研單位的大院。孩子們不是北京本地的,是跟父母一起,天南海北來的。我們和本地人聯繫不深,特別單純。到了高中,一個全是女生的環境,勾心鬥角,你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懷疑,會被看成別有動機。
而那個年紀,你那麼需要集體,需要肯定。我本身又不是那麼勇敢,那麼倔強。
於是我就把自己收了起來,這一收就是十幾年。等於是說,一個女孩,還沒來得及放肆,叛逆,犯錯,充滿稜角,釋放激情,還沒有把自己的好與不好統統都拿出來,一切都還沒來得及,就把自己給收起來了,像一把傘一樣。我甚至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樣的,就把自己給封閉了起來。為了生存下去,為了保護自己。
就這樣,我長成了一個小心翼翼的女人。但是,我心裡是期待這把傘能盡情張開的,在大雨里盡情的張開。
「我曾經害怕創造,因為需要能力。」
小時候,我害怕自由,害怕選擇,害怕創造。我想過一種安全無趣,波瀾不驚的生活。說出來你不要笑,小時候我一直想當秘書。因為我覺得秘書的工作是最不需要創造力的,只要你聽話就好了,把文件放在那兒,把檔案整理好。你看,我們小時候對自己的理解,對自己的規劃,有多可笑,多可怕。
但是現在,我最害怕生活無聊,工作乏味,我希望一切都多變化,多創造,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賦予到別人身上。希望每個角色都不一樣,希望每段愛情都點亮我。希望自己不是建立在對方的悲喜上,有自己獨立的靈魂和生活。
你問我的明星生活里,最享受哪個部分?還是演戲,還是在現場。比如我拍《搜索》,就可以理直氣壯的推掉各種廣告拍照和活動,就一個理由:「我在拍戲。」我喜歡早晨起床,穿著最舒服的衣服坐在現場,等著劇本來。我喜歡換好衣服,化好妝,看著鏡子里的自己,心裡一直琢磨著今天的戲。我喜歡角色給我的一切,包括痛苦,包括崩潰。我心裡給自己一個時間期限,在此之前,我允許自己在角色里崩潰。這是一種創造。如果沒有創造,一切的工作都特別的無聊。
演戲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在其中我成長為我自己。
「在崩潰和爆發中,我認識了我自己。」
一切的變化是從《南京南京》開始的。那時,陸川對我說了一句話,至今對我都有影響。他說:「你在演的,是你想成為的自己,但不是真正的你。」當時我並不能真的理解,但是我開始思考:真正的我,到底是什麼樣的?
拍《南京南京》對我來說,是自我成長過程中,一個刻骨銘心的體驗。姜淑雲比我以往的每個角色都更有深度,而那個深度,是當時的我達不到的。陸川給我的否定,比前三十年加在一起的都多。內心孤立無援,角色本身又那麼絕望。把我逼到了一個極致的狀態:濃度很高,密度很高,很笨很拙,又極其堅持,極其較勁。就像一根繩子綳到了最緊。
那個時候,剛好又是(夏雨袁泉)那個新聞事件。我真的是被逼到了一個死牆角了。其實一路走來,我還是很順,從來沒有遇到過那麼多誤解和侮辱,我真的是百口莫辯。這一切都把我壓到了一個爆發點,我索性就想:「我不管了,我管你們幹嘛,愛怎麼著怎麼著,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我豁出去了。」我跟自己說,你就先放吧,只有把自己給放出來,你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你自己。
別人說,北京女孩兒特別靠譜,是因為崩潰來得特別早。十八九歲就崩潰完了,二十多歲開始重塑人生。到了二十五歲心靈飽滿肉體充實,一過三十,完全是日臻化境的優越感和目空一切的才華。而我是反著來的。崩潰和爆發,都來得特別晚。遲來的青春期,在內心反而走得特別長。
逆生長,我喜歡這個詞兒。不是說越活越回去,越活越幼稚,是說,越活越來勁,越活越勇敢。到了三十多歲,我一點一點張開自己,一點一點收集自信,打破自己給自己的限制,去活得興高采烈,盡情盡興。
「原來我挺二的,兩個白羊,那就是橫豎都是二呀!」
多年以來,我一直自認是個標準的天枰座。尋找平衡點,自以為很溫順,是脾氣很好的女孩兒,是個淑女,等等等等。就在這時候,我突然發現我的月亮和上升都是白羊!這給我的震撼太大了,兩個白羊,那就是一個「井」字——橫豎都是二啊!
我頓時就釋然了。其實我性格里的另外一面,又二又衝動,又暴躁又任性,莫名其妙的天真,莫名其妙的堅持,為了賭一口氣,做事不計後果,從來都不是計劃好了才做,一掏心窩子就不行不行的……
我都是不願意接受的。它們都在,但是我選擇不接受。星座就是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這個時候我一下子都接受了:因為我有兩個白羊啊!哎呀這是你的命你就認了吧!心裡突然變得特別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