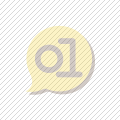摘要:那時他剛進斧頭幫。因剃著光頭,便喚作了光頭林。斧頭幫人人都有把斧子,極小,幾乎能裝進兜里。
那時他剛進斧頭幫。因剃著光頭,便喚作了光頭林。
斧頭幫人人都有把斧子,極小,幾乎能裝進兜里,這斧子並非用來砍殺,而是投擲——行話叫作「丟彈子」。剛進幫月余,光頭林便已練出了準頭,十多米外的一隻酒瓶,他一斧子飛去便是「嘩啦」一聲,基本不會失手。但他還沒用斧子扔過人。
斧頭幫的對頭是金龍幫。金龍幫人少,地盤也小,但老大鄒德清卻極精明。鄒德清瘦高個,戴眼睛,走路時略顯佝僂,手中常握一隻煙斗,說話也是輕聲慢語的,一副精明相擺在了臉上。鄒德清在此地人頭熟,和各位大佬說得上話,更主要是和斧頭幫打交道多年,對斧頭幫老陳的套路極熟,只要老陳想玩花活他總能棋高一著來個反擊,所以金龍幫雖實力弱,卻一直稍佔著上風。
老陳很清楚,金龍幫所倚仗的只是鄒德清一人而已,只要鄒一倒,金龍幫便會任自己捏弄。
為除掉鄒德清,老陳曾三次找過職業殺手。不過鄒德清也早防著這招,在城中遍布眼線,消息極靈通,其中兩個殺手甫一入城,便有人前來送禮,打開一看,卻是四隻發紅變質的湯圓——江湖規矩,四隻湯圓代表四目相對,四隻發紅的湯圓,其意可想而知。在湯圓旁還另附有支票,金額與老陳的懸賞相同。見行蹤已露,殺手也不敢收「禮」,便即返回。
另一殺手倒是瞞過了鄒德清,不過鄒德清平日不輕易出門,出門時也極小心,幾乎不露破綻,那殺手一時找不到機會,稍耽擱幾天便也露了行藏,仍一樣被打發掉。
老陳見此只得轉換路數,想在幫內找人,不過這極是冒險——殺手為幫內之人,一旦失手被捉便毫無推脫的餘地。這令老陳頗為頭疼。
那天巡視幫里,見光頭林正練「丟彈子」,老陳不由得心裡一動——這光頭林剛入幫一個月,幾乎無人認識,出了事完全可想辦法推脫,且這小子看來蠻靈光,剛練一個月便已有這般準頭,如把槍法練一練的話……
老陳便揚手叫過光頭林,也不多說,只塞了幾張票子,讓光頭林去某射擊俱樂部玩玩槍去。
過了一周,便又交給光頭林一支獵槍,讓他去郊外打打野物。回來後,老陳問收穫如何,光頭林搖頭道:「沒一槍打中,那俱樂部的槍怕是做過手腳,準星是歪的,練半天全都白練。」老陳不由一笑:「還行,小子有點悟性。」
接下來便練了一個月的狙擊。這光頭林似天生是玩槍的,無論何種槍,玩上兩天便心中有數,再開槍便已八九不離十,而且他還尤擅打移動靶,那天在郊外,他兩次用狙擊槍打下了飛行中的野鴿,竟連瞄準鏡也未開。老陳看得有些發愣:這樣的槍法,竟是只練了一個月,誰能相信?老陳連連點著頭,心裡卻有些嘀咕——這他媽的,也太那個了,他想。
老陳對光頭林說了計劃——他想光頭林早應該猜到了。果然,光頭林沒半點猶豫,滿口應承下來。
待光頭林走後,老陳卻開始尋思:媽的這小子也太精了,當面應承得好,回頭會不會跑掉?
老陳想應該找幾個人盯著他,但又一轉念:唉,算了,跑就跑了吧,也不算個事。
光頭林倒確實是想跑——刺殺鄒德清,這連職業殺手都完成不了的事,自己能行?
然而不知怎麼,心裡卻又似隱隱地有一股勁,促著他去試試。一隻風箏總得有根線牽著,他覺得這事就像是那根線,它勾在心上,讓他掙不開也跑不了。光頭林覺得心裡很亂,一會兒很興奮,一會兒卻又似害怕得緊。
鄒德清仍是深居簡出,不過每月他必去幾次賭場。這也幾乎是僅有的刺殺機會。
賭場靠近鬧市,四周是商務樓、酒店、飯莊,不太容易找到伏擊地點,且一旦開槍,便極難脫身——所以之前的殺手未能找到機會。
不過打一開始,光頭林就隱隱有個念頭:伏擊地點不必在附近,可以遠些,甚至遠至極限處。他用的是M40狙擊步槍,有效射程八百至一千米,不過光頭林知道,M40最長的狙殺距離可達一千五百米。
一千五百米,一公里半,如此遠的距離,開槍後當然可以從容脫身,至於打不打得中么——咳,反正是憑運氣,試試。
光頭林找了一圈,最後看中了一處爛尾樓,這樓只一個框架,十幾層,也無人值守,只幾個乞丐以此為家、早出晚歸。而此處也正是鄒德清去賭場的必經之地
爬上樓頂,卻見那賭場正遙遙相望,中間一幢高樓阻隔,卻恰好露出賭場大門的位置。用望遠鏡看去,那裡的人勉強可辨面目。光頭林心中不禁打鼓,「應該也出不了什麼事,碰碰運氣罷了……,」他心裡對自己說。此時他並沒認真想過殺人,他覺得自己肯定打不中的。
守了四天,那天下午鄒德清的車終於來了。光頭林盯著那車,覺得背上的汗毛正在一根根立起。轉瞬間車已到了賭場,鄒德清最後下車,他戴上帽子,左右看看,然後夾在三個隨從中向大門走去。
光頭林瞄著那身影——距離太遠,已不能瞄準具體部位。心裡本一直猛跳的,此時卻忽然穩下來,似有一隻手在心裡輕撫一下。腦子裡似有纖細的水草划過,想抓,卻又已漏過,心裡不禁痒痒的。只在這片刻間,光頭林似已模糊想到:嗯,這他媽就是自己要做的事,命中注定的。他屏住呼吸,心裡莫名一嘆,竟說不出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