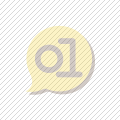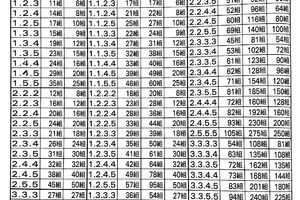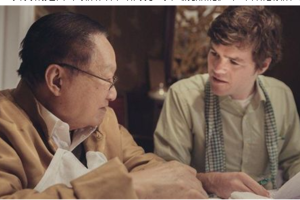摘要:母親平靜地說,我懂的,這個世界上處處都是出賣上帝的猶大。我的心像是被什麼剜了一下,疼,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1
記得奶奶生前坐在大門邊滾葉煙時,自言自語說過一句話,我是沒人寫,要寫,我這輩子也能寫出一本書來。那時我正坐在屋檐下的馬紮上,咬著筆頭為一篇作文急得跳腳。心想,得虧我不會寫,會寫我也不會寫你,哼!
我討厭她就跟她討厭我一樣,我也不知道是哪得罪了她。按照村裡所有人和親戚六眷的看法是,她重男輕女。她的重男輕女表現得明目張胆。出門走親戚,她的肩膀是我哥的大路,而她卻不肯背我走半步。有什麼好吃的,也是先緊著我哥,一碗水從來沒端平過。為此我母親還跟她理論過。我母親說,鶯妮子又不是我偷人養漢生出來的,您怎麼就這麼嫌她。奶奶臉色一暗、身子一旋說,我就嫌她,你能把我怎麼地?我母親頓時胸間作梗。母親原以為奶奶會喊聲冤枉,畢竟孫女兒一天大一天,心太偏了,恐記恨。可她壓根就不在乎。經此一鬧,她對我更加厭惡了。比方她炒菜,我和哥哥聞香進廚房,哥哥用手在碗里夾菜吃,她就會說,餓了吧?乖乖,飯快好了。換成是我,她就會用鍋鏟把打我的手,說,一個女孩子家家,像什麼話,你餓死鬼投胎嗎?還比方在稻場上乘涼,她手裡的蒲扇時不時就會很輕柔地掃過我哥的身體,而一旁的我都快要被蚊子給抬走了,在我忍受不住大吵大鬧時,她的蒲扇就會「撲撲仆」像擂鼓般打在我身上。
那時我們村經常有賣小吃圈巷的,那些貨郎每次從我們家門前過就會高聲嚷嚷,麻花燒餅咯,麻花燒餅咯!我和哥哥飛出屋。哥哥說要吃,她就從褲兜里拿出手絹細細展開,抽出一角兩角錢遞給哥哥。我要吃,她就說,問你媽要去。見我看嘴的樣子可憐,她才從哥哥手裡給我掰下一小塊,狠狠塞到我嘴裡,說,吃,吃。
我從小就沒得到過她半句好話,不僅如此她還在親戚面前四處敗我,在大姑家說我好吃懶做,被父母嬌成了一屁樣;在舅爺爺家說我是豬油和尚,讀了兩個學前班連二加三等於幾都不知道;在姨奶奶家說我脾氣大,大人說一句,絞嘴絞翻天。於是逢年過節親戚們一攏堆,十幾張嘴巴就擱我一人身上,說得我伸手手錯,伸腳腳錯,逼得我倒剪著手,貼著牆根一動也不敢動。而她卻在一旁悠然地吧嗒著葉煙,嘴角露出一縷笑容,做出一臉滿意狀。
我哥祝鴿被她的偏袒和溺愛縱容得鬼精鬼精的。一有客人來,他就會迎上前,然後沖外高聲喊上一嗓子,鶯妮子,快篩茶。礙於情面,我不得不撇下我的夥伴和跳洋房子的瓦片,跑到屋裡汗流浹背地找茶杯倒開水。因為被動接受勞動,行動上免不了衝天摔地,情緒上免不了嘟嘴板臉,茶端到客人手裡,客人還不領情,他們依然表揚哥哥,說祝鴿到底是大的,待人接物,禮數周到。這算什麼呢,他就憑一聲喊收買人心,而我做了實事卻吃力不討好。再有客人來,哥哥再喊,我就會高聲回一句,要篩你篩,別得了便宜又賣乖。
奶奶趁機向客人進言,這妮子就是懶,這要懶在致命的位置上,非懶死不可。我聽到了跟沒聽見似的,批評的話聽多了耳朵就油了,再難聽的話到了我這裡有如東風吹馬耳一般。我在上學前班時老師就當眾誇我,說,祝鶯鶯小朋友經得住表揚也受得住批評,是個好孩子。
寵辱不驚,別人需要大半輩子的時間才能修成的境界,我打小就練就了。
還是先來說說我生活的鄉村吧。
我所生活的村莊位於鄂西南角處,村名叫腰店子。其實我至今都很羞於向外人說起它的名字。這個彷彿是用腳趾頭想出來的村名曾一度令我感到自卑與鬱悶。別人一問你哪村的?
腰店子村的。
腰店子!好奇怪哦,還有叫腰店子的說,是不是還有肺店子膽店子尿水脬店子啊?繼而便是一陣鬨笑。
我這小臉都被這該死的「腰店子」給丟盡了。
在我讀書學會查字典後,我就立志一定要給腰店子換個叫得出口的名字。我說,叫柳花村、桃花村、桐花村。奶奶納著鞋底,長長的硬棉線勁鼓鼓地「嗤嗤」作響。她說,叫什麼都不如腰店子好,腰店子是現在落魄了,解放前熱鬧得跟縣城一樣,長長的一條街,都快通到你們學校門口了,這名字還是你們太公公起的呢!
奶奶說,你們太公公給人看完病後回家,經過這裡,說是親眼看到一個金雞母引一窩金雞崽「喳喳喳」地叫,你太公公下了兜子走近一看,又什麼都沒有,回到兜子上再一看,確確實實是一個金雞母引的一窩雞崽。太公公什麼樣的人,走南闖北不知見了幾多大世面,認定這是塊風水寶地,當即就在此買了一百多石田,修了個醫館,聽說是祝先生開的醫館,十里八鄉的病人都來這看病,藉著醫館的人氣,慢後才有了飯館、肉案、包子鋪、裁衣店、紙匠鋪、打鐵鋪、油坊、棺材鋪、雜貨鋪……因了你們太公公的醫館居中,向病人介紹位置的時候就說腰上的店子,於是就腰店子腰店子叫了下來,過去四方走馬販貨的人都知道西南角有個叫腰店子的地兒,是有名的當口。
我聽得目瞪口呆,原來這丟人現眼的地名跟祖上竟有牽連。我為此感到些小小的驕傲。逢人再問你哪個村的,我說腰店子的。在人笑過之後,我便會不緊不慢的附上我太公公這段公案,直聽得那幫小兔崽子們眼睛都定了神。
長大後,我一直琢磨,腰店子是不是藥店子的諧音,被人給叫訛了。
2
我們祖上行醫,世代的中醫,口授心傳,不知道傳了多少代。聽說有一位曾祖做過朝廷的御醫,還被賞了頂戴花翎呢,還鄉時帶了位不知是公主、妃嬪還是宮女的女人到腰店子落了籍。腰店子轉魚台土地那兒有個墳,村人管它叫娘娘墳,都說這娘娘墳里埋的就是我曾祖從京城帶來的女人。
至今我們村都保留了很多與醫藥有關的地名。村公路腳下的大堰叫藥鋪堰,村公路岔開的一條通往我們家的小路叫藥渣子路,與藥鋪堰隔路相望有一口井叫湯藥井。據說這口井是我們另一位曾祖挖的,井旁魚腥草成堆。村人熬藥大都取這口井的水,還順帶著揪一把魚腥草回家,說是清熱敗火最好了。後來這口井被越傳越神,說是這井水熬的葯,病不僅好得快而且還斷根。
奶奶說,那個時候,因了藥到病除的醫術,祝家不僅救死扶傷,還給人說公了事,威望很高,算得上一方鄉紳。你爺爺生前總說,不為良相,就為良醫。到了你爸爸手中,他不學醫,一本《湯頭歌》背了十幾天,還是「麻黃湯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這開頭兩句,你爺爺說你爸爸沒學醫的天分,就算了,後來供他讀書,當老師,照我看當老師沒有當醫生好。
奶奶一直對咱家醫術斷代深感遺憾。她希望後代中有人能把這個代接下去。哥哥考學時,她堅持哥哥學醫,也建議我讀衛校,但是我們都志不在此,她連連感嘆,後繼無人。父親後來身染沉痾,倒床不起,面對高昂的醫療費用和黑心斂財的庸醫時,也深深體會了奶奶的心情,再三叮囑我跟哥哥,後輩中一定要讓一個孩子學醫,學中醫。父親美好地認為,中草藥乃上天所賜,賤而養人,使病者不必花費許多錢財卻能使身體康健,既是上天的德也是醫者的德。
在村裡,奶奶的輩分最高,沒有一個人稱她為姐啊妹啊的。與奶奶差不多年紀的老人都稱她為麥嬸娘,晚一輩則稱麥先婆,再晚一輩則是麥太太、麥老太太。由此我知道了她的小名叫麥兒。跟她吵架吵輸了,我就跑到稻場里大口大口地叫麥兒麥兒。而她則順手抄起傢伙向我砸來,碗啦、茶杯啦、楊杈掃帚啦,有一次,向我飛來的竟是一把椅子,要不是我躲得快,險些就命喪椅腳。她很是混賬,不過討她的光,我和哥哥從娘胎里出來就有人稱我們大爹、小爹。母親說我跟哥哥是村裡的兒前輩。
奶奶很白很胖,一富態像。奶奶的髮式跟村裡其他老嫗不同。奶奶不像她們蓄髮攏結在腦後用簪子挽個揪,那些老人頭髮脫得厲害,與其說是揪還不如說是打的疙瘩,小氣。奶奶頭髮厚,剪的是如學生頭一樣的短髮,然後用個黑色的軟圍梳將頭髮打網似的攏到額頂,頭髮根根後倒,露出滿滿一張臉和兩隻厚耳,乾淨利落,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