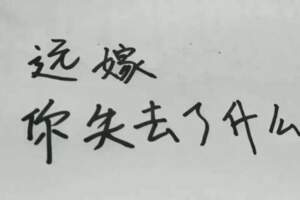「大旭,快進屋快進屋。外面老冷了吧……」暖意撲面而來,除了屋子裡的熱氣,更有姥姥的聲音和笑顏。我笑著應著,脫下鞋子,進屋與她嘮著體己話兒。
由於買不到過年間的返程票,一年未歸的我決定利用婚假回東北看老人,妻子體貼地答應了。
冬天的吉林天黑得特別早,到姥姥家時雖然才下午5點半,但天已黑透了。「聽你說得晚上才到,我這其實還沒都準備好呢,先湊合吃飯吧。」在火車上,姥姥的電話就不時地打過來。「我們出去隨便吃口就好,平時也沒這麼早!」「都做好了,趕緊來趁熱吃吧。」餐桌上,姥姥掀起扣在碗上的小盆兒,露出了她專門給我們炒的酸菜肉絲,還有新燜的大米飯。在我兒時住在姥姥家時,她總會做給我吃,在她和我共同所有的記憶中,這是我最愛吃的東西;每逢過年,要是能買到點好豬肉,她總會給我加到裡面,讓我一個人「獨享」,炒一大盤,能吃上好幾頓。
姥姥已84歲了,身體也一直不太好,自從前年姥爺走後,她便自己住了,最近又開始打針,平時由舅媽和大姨給她送飯,今天還得特意下廚給我做飯,不由得讓我有種愧疚感。我一句客氣話說出口,便被老太太「呵斥」了,只得笑笑不敢再提。飯後刷了碗,又嘮了幾小時磕兒,說的都是彼此一年的境況。
第二天,我早早起來,做了她愛吃的熗湯麵,飯後便陪她去打針。天氣濕冷,地面硬滑,樓門口的一小段路走起來很不易。打車到了醫院,姥姥不讓我再攙著,她左手扶著欄杆,一步一階地爬著樓梯。每走一層,氣息就變成很粗,便得停下來歇上一會兒,看著她蹣跚的步伐,心裡不禁一陣反酸。
一上午的吊瓶總算打完。回家的路上,她自說自話地跟我講著為人處世的道理,要我多做少說,多包容少計較,我滿口應著。中午做晚飯後,我們又開始聊;午覺後,她便在屋子裡來回踱著,或者用放大鏡讀《聖經》,在卧室里祈禱,我便繼續準備著晚飯。晚飯過後,我們一起看了她每天晚上都在看的電視劇《地雷英雄傳》,9點10分,她便如往常躺下睡了。
一連半個月的日升日落,都是這樣循環而過的。
姥姥說,你年前回來,都看不到你哥和大舅他們,大年三十那天肯定特別熱鬧,你在的話會更好,一起放炮打牌看春晚。我卻覺得,熱鬧的新年團圓雖令人嚮往,但是能在老人孤獨的時候能夠陪在她身邊,對他們而言,遠比過年時的團聚更加難得。
看似枯燥簡單的幸福日子,沒有網路、沒有牌局、沒有娛樂活動,有的只是最深情的關懷和三兩小菜。和姥姥一起居住的這些天,看著她每頓都有熱乎飯吃,陪她打針、陪她說話時她開心的神情,我收穫到了比過年時的熱鬧和團圓更加讓我滿足的快樂。
「一個人兒在家平時都干點啥呢?」「你老舅每天下班都來看我,陪我說說話,給我捶捶背。身體舒服時去教會,平時身子總覺得累,除了打針也不出門……」離開前一天的下午,我出去買菜回來,她沒有聽到我回家,我在門口默默地望著她,她在靠近窗檯的沙發上坐著,晴好的陽光映著她的臉龐,本已很駝的背比去年更彎了一些。她閉著眼鏡,雙手合十,嘴裡不停地嘀咕著什麼,雖然我根本聽不清,但禱告的內容,一定是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健健康康,順順利利。當晚,我做了她最愛吃的炒蒜薹、豆芽和鍋包肉,自己倒了一杯酒,算作我們之間的「年夜飯」。我最喜歡看她使勁兒咬鍋包肉的樣子:「慢點吃,多吃點兒!」二十幾年前她最常對我說的話,現在也是我對她說的最多的。
「年味兒淡了。」身邊的很多人都這樣說,尤其是置身城市的喧囂之中,每一天過的好像都是那麼的「熱鬧」;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小時候盼著過年時吃魚吃肉的興奮感,也消失地無影無蹤。走走親戚、看看春晚、朋友聚聚,轉眼年也就算過了。歸途的旅人奔著若隱若現的前程,離別的夕陽映出依依不捨的深情……於我而言,以前每一年的「年感」,也就是在與親人分別的一刻時,才提醒我,這「年」彌足珍貴。那天我拎著行李下電梯時,一直按著電梯門,她也就那樣一直開著門,我讓她關門、她讓我快下樓,結果就這麼僵持了五分鐘。最後,我跑出電梯,好好再抱了一下這個比我矮上兩頭的老人,並許下了「豪言」:「只要稍微得空,我還來看您!」
電梯的門終於緩緩關上,我知道,她仍會是那張淚中帶笑的神情。
盼著過年,不過是盼著回家,見到那些你朝思暮想的、把你當珍寶一般捧在手裡養大的親人。不是因為要過年,所以才回去,看看那些你在人生路上以奮鬥太忙、工作太累為由而忽略的人們,而是因為有了你的陪伴,那些在孤巢中翹首以盼的老人,才有了過年時的欣喜和歡樂。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有這份念想和陪伴,每天都是過年。
別讓愛你的人等太久,常回家看看,人言愛情是長情的陪伴,親情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