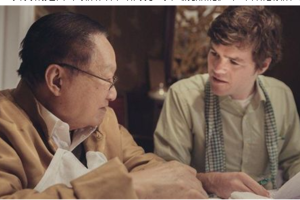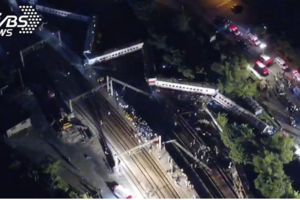| 亞普菲蘭特王國簡介 曆史起源于西元一五三0年,神聖羅馬皇帝卡爾五世冊封旗下一名部將古斯塔夫·馮恩·舒伯恩佛特為薩爾斯蘭特邊境伯爵。因為古斯塔夫在前年與奧斯曼土耳其軍隊發生的維也納攻防戰當中建立了顯赫的功勳。舒伯因佛特家于一七世紀末血統斷絕,由姻親修陶匹茲家繼承邊境伯爵稱號。同時趁機進獻南方領土給皇帝,變更國號為亞普菲蘭特公國。在拿破侖戰爭之後改稱為王國,直至今日。民族以德國人為主,亦有北斯拉夫人。語言德語(高地德語)。宗教以天主教為主。地理位置位于歐洲中央位置,四面接陸。東邊為俄羅斯屬地波蘭,北邊為德意志屬地西利希亞,西邊為德意志屬地薩克森,南邊為奧地利·匈牙利屬地波希米亞。領土面積一萬三六六五平方公裡(一九0四年資料)。人口一0四萬八九二0人(一九0四年資料)。首都夏洛蒂布魯克。元首卡蘿莉娜二世(一八七四年登基)。主要產業農業、畜牧、林業。由于過去曾經大量出產岩鹽,最早被稱為「鹽之國」。 Ⅰ提到西元一九0五年,眾人皆知當時法國著名的高中生偵探易吉道·波特雷在荒涼的諾曼第海岸發現了神秘人物亞森羅蘋的藏身之處。(譯注:此段指的是推理小說亞森羅蘋系列「奇岩城」內容。)這一年的歐洲尚稱和平,然而一月間,在俄羅斯帝國首都彼得格勒(聖彼得堡),軍隊朝著舉行和平遊行向皇帝請願的民眾開炮。這次「血腥星期日」事件成為俄羅斯日後革命的導火線。在非洲,英國、法國、德意志為了爭奪摩洛哥統治權,各國如同狂犬般相互叫囂。在亞洲,日本帝國繼日俄戰爭之後,接連在陸戰海戰告捷,乃木司令官與東鄉提督的大名遠播至歐洲一帶,然而日本的國力亦已衰竭,無法繼續開戰,于是努力尋求和平談判的機會。學術方面,艾伯特·愛因斯坦(譯注:AlbertEinstein)發表高深的「相對論」學說,可惜由于理論過于深奧,一般人無從理解。此外,謝文定(譯注:Schaudinn)與霍夫曼(譯注:Hofmann)兩位醫生發現梅毒這個可怕的疾病。飛機在兩年前由美國的萊特兄弟(譯注:WilburWright與orvilleWright)發明,一年前德國庫傑爾發明鎢絲燈泡。挪威探險家阿蒙森(譯注:RoaldAmtmdsen)發現西北航線的完整路線,並與英國探險家史考特(譯注:RbertfalconScott)相繼抵達南極。這一年,法國的儒勒·凡爾納(譯注:JulesVems,法國科幻冒險小說家,著有「海底兩萬哩」、「環遊世界八十天」。)結束了七十七年的偉大生涯。德意志的路德維希·湯瑪(譯注:lmdwisThoma)出版「惡童物語」(譯注:LausbubensesChichten)」。萊特·海格(譯注:HenryRiderHaggard,奇幻文學作家。)四十九歲,亞瑟·柯南·道爾(譯注:ArthurConandovle,英國推理小說家,著有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四十六歲,莫裡斯·盧布朗(譯注:MauriceKeblanc,法國推理小說家,著有怪盜亞森羅蘋系列。)四十一歲,哈伯特·喬治·威爾斯(譯注:HerbertGeorseWells,英國科幻小說家。)三十九歲,卡雷·查派克(KarelCapek,捷克科幻小說家,著有「羅梭的萬能工人」),阿嘉莎·克莉絲蒂(譯注:AsathaChristie,英國女性推理小說家。)十四歲,埃裡希·凱斯特納(譯注:ErichKasmer,德國兒童文學作家。)六歲,喬治·奚孟農(譯注:GeoresSimenon,法國推理小說家,著有馬格雷警長探案系列。)兩歲。再過不久,小說將從少部分人的私有物拓展成為多數人的公共財產。這個時代的人們深信科學代表進步,進步代表幸福,這樣的故事只有在這樣的時代才可能發生。亞普菲蘭特王國的首都夏洛蒂布魯克之名取自十八世紀前葉在位的一位女王名諱。此位人物並未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實績,只是讓人們借由城市名稱記住此人罷了,姑且不論如何,夏洛蒂布魯克是個風景秀麗的城市,從新舊風格搭配協調的成排建築可以遠眺淡紫色山脈,五月初搭乘特制火車從東邊進入夏洛蒂布魯克的旅行者應該也能望見倘佯在春末微風之中的街道。圍繞在亞普菲蘭特四周的群山並不像阿爾卑斯那般險峻。標高大多一000到一五00公尺,山頂積雪到了四月便會融化。取而代之的是綿延到山頂的濃密樹叢,木材資源富饒,野生動物種類繁多。一到五月,森林豐沛的生命力持續向藍天萌芽,濃密的綠意化為一片綠光布滿人們的視線。即便從火車的車窗玻璃得以望見這幅能夠放松眼睛的美景,可惜也僅是浮光掠影。火車一接近夏洛蒂布魯克車站的區域,一名身穿老舊軍裝、表情嚴肅的彪形大漢便走上前,一把將車窗的窗簾拉下。坐在座位上的少女整個視野馬上被鎖進昏暗的包廂內。彪形大漢以粗厚的皮膚擋回少女抗議的目光。「等天黑才能下車。」彪形大漢以刻板的語氣說著平板的語句,語畢便走出車廂。才要離開,額頭便跟門上的橫梁撞個正著,發出偌大聲響,只見他連睫毛也沒動一下,繼續彎身穿過門口,聲響再度傳來,阻斷了走道的亮光。當門一關上,少女挾帶著憤怒與不安,直瞪著已經消失的大漢背影。少女左手一擡,隨即傳來鎖鏈聲,少女的左手腕上套著一個鐵制的細環,延伸出來的鎖鏈連到左腳踝銜接另一個鐵環。鎖鏈的長度不至于綁手綁腳,但要阻止她逃脫卻是綽綽有余。要挂著這副鎖鏈全力奔跑,則必須同手同腳才行。少女不耐地甩了甩披肩的秀發,目光盯著窗簾,盯著包廂座位上收成圓條的毛巾,盯著小茶幾上的花瓶,終于下定決心准備站起身之際,門又再度開啓,走道的光亮傾瀉而人,少女僵著表情與身體,凝望著無聲無息走進來的黑影。那不是狗,長得像貓但又比一般的貓還大,身長約是少女的兩倍,體積也是兩倍大。身上的毛皮閃著黑色光澤,宛如由黑曜石的粉末制成,直視少女的炯亮雙眼透著黃玉色澤。體積比老虎小,比豹大,只能確定是肉食性的貓科動物,其它一概不詳。少女倒抽了口氣往後退了一步,黑色怪物則配合著往前踏出一步。流暢的肢體動作以優雅一詞形容也不為過,然而這就等于認為鮮血的顔色很美一樣。怪物口中發出低沈的威嚇鞭打著少女。「安靜,阿奇拉,不准亂叫。」一名女子出聲制止猛獸,黑色怪物立即打住吼聲,稍稍調整姿勢,看起來就像准備迎接國王的儀隊士兵。怪物從門扉正面走到一旁,騰出一個只讓軍人通過的空間,接著聲音的主人現身,無庸置疑地,是一名女性。女子外表接近二十七、八歲,再過一、兩年或許便可具備成熟女性所應有的美麗與魅力。接受過陽光洗禮、透著暗金黃色的粟發剪得極短,如果留長應該是一頭漂亮的卷發吧。姣好的柳眉仿佛刻意描過一般,下方晶燦的藍色雙眼充滿了咄咄逼人的氣勢,充分彌補了欠缺個性的端正口鼻。最令人注目的是她身上的服裝,她和她猙獰的寵物同樣是全黑的扮相。她頭上戴著的不是無邊女帽,而是高禮帽;身上穿的不是絹制禮服,而是男用長禮服;手上持的不是陽傘,而是手杖。當時流行的最前端是巴黎,這名女子的打扮不是巴黎的淑女,而是巴黎的紳士。「格茲向來沈默寡言,想必沒有對你說明清楚。」女子提到的人名,指的應該是拉下窗簾的彪形大漢。「由于某些因素,必須等天黑才能下火車,你能不能再忍耐半天左右?」「我已經忍耐不下去了。」少女咬牙一字一句反駁回去。「我不會追究你們之前的種種行為,快放開我。」「有個問題,就是你從你祖父那裡繼承過來的遺產,先解決這事再說。」「律師說依法沒有任何問題。」「依法呀,政治跟物欲向來無視法律的存在,真是傷腦筋呢。」女子聳了聳披著男用長禮服的肩頭,這段對話所使用的並非亞普菲蘭特的公共語亦即高地德語,總之這只黑色野獸完全聽不懂,對于主人的不理睬只有擠出白牙,輕輕打了個阿欠。「天黑以後所有必要文件都會完成,希望你在上頭簽名,小姐。」「我如果簽了字會怎麼樣?」「當然是一輩子不愁吃穿,因為我會付給你一大筆報酬,不過要請你先等個半年。」「那如果我不簽呢?」「應該也是一輩子不愁吃穿吧。女子的朱唇勾起嘲諷的曲線。「因為你已經不需要吃穿了,不過我並不想動粗,希望你明白。」少女保持緘默,露出一副不想理解的表情。見了她這副模樣,女子的眼角閃過近似無奈的神色,她認為現在說甚麼也無法說服少女。「不用急,我們可以慢慢聊,希望你能做出合乎二十世紀年輕人應有的聰明抉擇。」女子以手杖敲向地板。「不需要關門了,阿奇拉的毛皮比三0公分厚的鐵板更可靠。」女子對著猛獸投以信賴的目光,她的視線看來並非是在看待寵物而是一個朋友,一旁盯著他們的少女假若再增加一些人生的曆練,或許就可看出這段超越種族的友情。女子轉身離去。這只名叫阿奇拉的漆黑野獸用它那黃玉色的眸子盯著少女,發出屬于聽覺範圍等級最弱的低狺,那是享受著少女的厭惡感與恐懼感的魔性吼聲。Ⅱ夏洛蒂布魯克無庸置疑是亞普菲蘭特最大的都市,人口約有一0萬之多,但還不及巴黎市內的一區。由花崗岩與紅磚砌成的建築物最高也只到四樓。皇宮位于市區中心,前方面對行政街,後方緊鄰貝潔湖。玄武岩堆砌的石牆高度還不到兩公尺,建築也是兩層樓,與氣派一詞相距甚遠,只能說小巧精美。某位由蘇格蘭來訪的公爵曾經表示:「比我別院裡的別墅還小。」說又說回來,國家這麼小,皇宮要是蓋得太壯觀也不是甚麼值得稱許的事。在這世間所謂門當戶對的確是必要的。威魯吉爾·史特勞斯簡稱威魯,這一天仍然按往常一樣七點就睜開眼。他居住的閣樓間天窗正好向西,陽光不會曬進來。但他一向都是自然醒來,不用人叫。威魯從牢固的軍用睡鋪上坐起身,打了個大大的呵欠並伸展手腳,一只手邊搔著顔色平凡無奇的茶色頭發一邊下床。威魯今年十四歲,身高與年齡成正比,有著結實敏捷的健康身體與一雙如同接受過夏日豔陽洗禮的常綠樹葉般的晶燦綠眼。十二年前母親過世,九年前父親過世,三年前祖母過世,從小學畢業以後這兩年來一直自力更生,這就是他的經曆。所幸他的祖母教導他足以養活自己的一技之長,只是經常被警察抓。其余時間他也是會從事正常工作,例如到蘋果園幫忙、塗油漆、修理馬車等等。祖母留下一筆為數很少的小錢給威魯,但最令他自豪的是他從來沒去動用過一毛錢,也不想去孤兒院或濟貧院寄人籬下。這個閣樓間除了一張床鋪以外,還有老舊的橡木桌椅、同樣老舊的小櫃子,以及軍用衣櫥,全部家具就只有這些。穿好衣服,拿出臉盆洗臉,漱完口之後,威魯便奔出房間,伴隨著肚子空空時響亮的咕噜聲,兩步並三步沖下窄小的樓梯。從小巷來到大街,轉過石板路的街角便來到目的地。這裡是來自波蘭的華勒夫斯基經營的小攤子,令人食指大動的香味跟著熱氣撲鼻而來。「早安,華勒夫斯基先生。」「早安,今天要吃些甚麼?」「牛奶!要攙蜂蜜而且是熱熱的那種,還要水煮馬鈴薯,幫我多抹點奶油哦。」「不要面包嗎?」「今天不要。」「不介意是昨天剩下來的話就送你幾個吧。」才道完謝,一個人影便動作遲緩地出現在威魯身旁,威魯不禁縮起脖子,華勒夫斯基則滿面笑容朝著剛來的客人寒暄。「剛值完夜班嗎?警長先生。」「是啊。」「是不是發生了甚麼大事或怪事呀?」詢問的語氣有一半出于好奇心,另一半是對警察的問候。默默搖頭的男子身材高大,比威魯高出將近三0公分,身穿常見的淡灰色西裝與西褲,只有松開的領帶呈現醒目的紅褐色。除了臉的下巴長滿了暗褐色胡渣,五官幾乎留不下任何印象。此人正是艾佛列特·法萊沙警長,這兩年來與威魯的職業八字相沖的公務員。「這個地方不會發生甚麼需要值夜班的事件,還不都是因為市警局局長大人不喜歡部下太過清閑,不說這些了,給我一杯咖啡。」「好,要加牛奶嗎?」「不需要,另外再給我黑麥面包跟……那邊的香腸還有蛋,蛋要半熟,香腸幫我煎焦一點。」趁著警長點菜之際,威魯迅速將牛奶與馬鈴薯塞進胃袋,同時以每秒一毫米的速度遠離警長。隨著一聲「我吃飽了!」,三枚銅錢跟著響起,威魯像只逃離陷阱的兔子飛奔而去。警長盯著他消失的方向,同時,華勒夫斯基隨即把盛著香腸的盤子遞到書長眼前。「警長先生,威魯是個好孩子,我保證。」「你真的這麼認為嗎?」「呃,是啊,那當然。」「既然如此你不如多關心他點,他總不能就這樣渡過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吧。」華勒夫斯基頓時跟先前的威魯一樣縮起脖子,然而法萊沙警長也無意繼續追究,開始默不作聲將早餐一掃而空。華勒夫斯基松了一口氣,這對自己跟小客人都好。對華勒夫斯基而言,大清早遇到警察總會覺得這一天的生意會不太順利;他對自己的功夫有十足的信心,最難得的是他也明白有時運氣會勝過實力。「霍克斯伯克斯·菲基布斯、霍克斯伯克斯·菲基布斯。」威魯步伐快速地走在路上,嘴裡哼著祖母說是她的祖母教的驅魔咒語。與其說是咒語產生效果,不如說是涼爽的五月風讓威魯的心情豁然開朗。若是老人也就罷了,但庸人自擾並不適合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威魯身上的茶褐色外衣是拿大人的衣服修改過的,他衣角飛揚地走在路上,汽車發出刺耳的排氣聲與引擎聲往反方向疾駛而過。德國人戴姆勒(譯注:GottliebDaimler)在一八八六年發明賓士汽車,一八九四年法國舉辦全世界第一場汽車大賽,本篇故事設定時間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0六年法國舉辦首屆GP大賽,令全歐洲賽車迷為之瘋狂。不過目前在亞普菲蘭特,馬車仍然占了壓倒性多數。以數量來看,汽車跟馬車的比例大約是一比一0吧。威魯喜歡鐵路,只要一天不到中央車站附近的天橋上看火車,他就會坐立難安。亞普菲蘭特雖是小國,不過由于地處歐洲內陸交通要沖,一天內會有好幾列跨國列車經過境內。火車的目的地有巴黎、維也納、柏林、布拉格、華沙、慕尼黑、基輔等地,從東方來的火車送來綿延到亞洲的大草原氣息,來自威尼斯的特快車帶著海水的芳香,至少鹹魯是這麼覺得。現在剛過上班上課的時間,天橋上空無一人。雖然只有短短的時間,但這座天橋現在正處于威魯一人的支配之下,他的眼下是寬廣的調車場,在光禿的紅土上有二0條以上的路線,幾何圖形的軌道或並排或交叉。威魯的視線由下往上擡,遠望環繞城鎮的山脈,低聲喃道:「我才不要一輩子窩在這個內陸小國裡,再過兩年我要到巴黎去。」威魯就是為此才努力存錢,要是口袋空空前往花都巴黎一定會很淒慘的。巴黎看不到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很高很高名叫艾菲爾的鐵塔。路燈不是煤氣燈而是電燈,萬國博覽會數年舉辦一次,全世界的觀光客大批湧入——總之就是充滿了夏洛蒂布魯克這個窮鄉僻壤所沒有的事物,威魯恨不得趕快投身那種熱鬧與繁榮之中。正當威魯透過鐵路與火車架構自己的夢想之際,這小小的和平卻即將在現實世界粉碎。才要緩緩駛過天橋下方的火車停了下來,最後一節車廂跳出一個男人,這個人蹑手蹑腳走上天橋樓梯,逼迫現實與夢想產生沖突。「小鬼,你在這裡做甚麼?!」金屬般的吼聲貫穿威魯的耳膜,不到半秒時間他感覺到空氣的振動于是立刻跳開,馬鞭隨即重重劃破空氣,這時威魯才發現已經躲過了一記羞辱的鞭打。等他的視線回到現實,只見天橋上站了一名男子戴著紅色高禮帽,身穿男用長禮服,打著領結並且別了一支看來應該是真品的祖母綠寶石別針。燙卷的小胡子下方泛起殘忍的笑意,兩眼直瞪著威魯。Ⅲ威魯並不算占了好地利,他背對著天橋的欄杆,男子只要做弧形移動就可以擋住威魯的退路。明白這一點的男子加深了殘虐的笑意,然後揮起鞭子,不料威魯撲上前,往男子身上一撞,雙方扭成一團,最後仍然被甩開的威魯本已經准備接過從頭頂落下的鞭子,結果並沒有。因為在此時突然有個男子出現在天橋,從長禮服男子手中搶過鞭子。威魯吃驚的程度並不亞于長禮服男子,原來救了他的是剛剛才在攤子尴尬碰面的法萊沙警長。警長凝聚沈穩的氣勢對著長禮服男子說道:「先生,我們這裡沒有鞭打小孩的習慣,請您先答應不把這條鞭子用在這孩子身上,我就還給您。」「……哼!這個國家的人就是懦弱怕事才會無法躍上世界舞台,你們就繼續做個連一塊殖民地也沒有的小格局內陸國家直到接受末日審判吧。」男子語帶惡意,兩眼直瞪警長,順手拍掉長禮服上的塵埃。警長不理會對方耍嘴皮子,故意鄭重其事地遞出鞭子,男子立刻默不作聲搶了過去,接著轉身帶著憤怒的腳步聲離去。威魯本來還想大吼一聲「王八蛋」想想覺得太粗魯了,只有做個嘴形了事。法萊沙警長順手整了整鴨舌帽,接著定睛俯視威魯,看起來像是隔著一團落腮胡望過去一樣。威魯先道謝之後連忙解釋:「謝謝你的搭救,可是我甚麼也沒做哦,我只不過在看火車,那個人就突然拿鞭子要打我。」「哦……」「那個人是外國人吧,是德國人嗎?」「不曉得,反正這陣子流行只要一有甚麼壞事就會全部推給德國人。」警長劈頭先嘲諷世態一番,接著以不友善的視線掃過少年的臉。「那……你真的甚麼也沒偷嗎?」「太瞧不起我了。」威魯挺起胸膛。「我真要偷了東西,怎麼可能留在現場晃去晃去,害自己被那家夥逮住,這個時候應該早就在貝潔湖畔睡午覺了。」「那就好,不、其實不太好,總之這件事先擺一旁,我問你,你到底在那裡做甚麼?」「警察沒必要問那麼多吧。」威魯的態度不禁強硬起來,事實上他並不如表現出來的那般情心滿滿。在他衣服的內袋裡塞著剛剛從那個看似外國人的男子身上扒來的錢包,要是被警長逮住搜身,他馬上會被當做現行犯,扭送拘留所。威魯稍稍移動重心,擺好姿勢准備全力沖刺,只見警長並無意當場逮捕威魯,威魯受不了對方的沈默,開始變得饒舌。「警長,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順眼,可是我只不過想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你就放我一馬吧。」「你認不認識漢斯·傑朗?」「不認識。」話題突然轉移,讓威魯有點摸不著頭緒。「聽說上星期他在波伊街被人偷走錢包。」「……」「錢包第二天就找到,但是已經太遲了,傑朗先生償還債務的期限正好是錢包遭竊的當天傍晚,傑朗先生無法還錢,房子跟工廠全數遭到扣押,他在絕望之余選擇自殺,屍體到傍晚才被發現。威魯無言以對,好像是上星期或是更早之前,他的確在波伊街對一個神氣兮兮的男人施展祖母傳授給他的扒竊技倆。他只拿走—枚金幣,第二天就把錢包丟在市政府大門前,原以為事情到此結束,沒想到對方會自殺。「我……」看著不知所措的威魯,警長簡短搭了句:「騙你的。」「騙我……」「我是騙你的,根本沒有漢斯·傑朗這個人,剛剛的故事是我編的。」恍然大悟之後,威魯氣憤不已。「太龌龊了!警察怎麼可以說謊話騙人!」受到指責的警長不動聲色,正面凝視威魯。「設錯,這是個龌龊的謊言,不過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件事,你堅持的想法只需人人一個龌龊的謊言就會立刻瓦解。」威魯找不到話反駁,只有保持緘默,警長則繼續說道:「我不是在教訓你,但是你想想看,哪天你有了喜歡的女孩,你敢光明正大告訴她說你的職業是扒手嗎?」「我沒有喜歡的女孩。」「總有一天一定會有的,依我看,現在對你好說歹說,還不如你將來遇到喜歡的女孩,自然會對你的人生產生重大的影響。」警長的大手輕捋落腮胡。「人真奇怪,很少為了自己,反而會為了心愛的人發奮努力。」現在的威魯完全不想為別人努力,不過他感覺得出警長這番感慨是來自他長年累積的人生體驗。「警長你有過這種經驗嗎?」「有過幾次。」「那對方呢?」警長並未立即答腔,只是從天橋的欄杆俯瞰下方。「人呀,有時候很難在緊要關頭發覺最重要的事物哪。」警長以大掌輕拍威魯的肩頭,接著跑步離去以鍛練自己的長腿。即使有些意志不堅,威魯到頭來還是沒有把他剛剛跟長禮服男子扭打成一團時順手扒走他錢包的事對警長說出口。誰叫警長亂編謊話嚇他,這叫以牙還牙!威魯用這個說法趕走內心對于一己行為怯懦的內疚感。他帶著感覺比實際來得更重的錢包,暫且回到自己住處。威魯只拿現金,而且也不會全數掏光錢包,他只抽走一張紙幣跟幾枚銀幣,其它原封不動歸還。有機會的話他會趁著錢包的主人不注意時,把錢包放回對方的口袋;再不然就是從市警局大樓的窗口丟進屋內。威魯自認最妙的傑作是有一次他扒了俄羅斯貴族一個蠻重的錢包,然後塞進市警局局長口袋。那個時候就看到那些人的表情一臉大便!威魯關上閣樓間的房門,小心翼翼再帶上門闩,接著把桌上的錢包用力打開。亞普菲蘭特處處趕不上歐洲列強的前衛腳步,警方迄今仍然尚未全面引進指紋比對的搜索方式,也因此威魯得以悠然自得靠雙于過活。「誰管那麼多,反正我又沒偷過窮人。」嘴裡之所以叼念個不停,是因為內心的罪惡感久久未去。「傷腦筋,全是外國紙鈔,dollor是哪裡的錢呀?喔、對了,是美國,法國應該不久就會用得到吧。」威魯一邊嘟嚷著一邊翻著紙鈔,突然一個異樣的觸感打中手指,這個東西跟紙鈔一般大,就夾在紙鈔當中。那是一張相片,相片上是一名少女,映入威魯眼簾的是一頭及肩的長發、凝視正前方的大眼睛及緊抿的櫻唇。Ⅳ好漂亮的女孩子,威魯贊歎著。相片下有一排文字,但威魯不會念,只確定那不是德文。威魯沒有上學!自然也沒有學過外語,他只有零零散散自修一些法語以備將來到巴黎之需。他翻閱從舊書店得來的法文辭典背單字,這本辭典不是偷來的,而是買來的。偷一個又老又窮的舊書店老板,是違反他的工作守則的,他把價錢殺到最低,乖乖付錢把書買回家。「也不是法文,是英文嗎?記得美國那個國家是講英語……」這麼說來,那個男人是美國人嗎?他有想過,可是沒有明確證據。威魯把照片仔細看了一遍,好幾個念頭在他腦子裡興起,化為片段的拼圖飛來飛去。當拼圖完成到一個段落,威魯決定采取行動,他把桌子搬到門前,關緊天窗,脫掉衣服疊好,然後鑽進軍用睡鋪。一切等天黑以後再說,先睡飽才好熬夜。想是這麼想,在睡鋪上輾轉反側了一個小時,威魯醒了過來,神志太清楚,根本睡不著。于是他再度穿上衣服沖出門去。當天直到日落之前,威魯嘗試了許多方法。雖然在中央車站被站員罵得狗血淋頭,多少還是搜集到了一些情報,接著再回到調車場,找出那個長禮服男子搭乘的火車停靠的位置。從天橋上直接俯瞰固然輕而易舉,不過他不准備這麼做.要是天橋兩邊被堵住就無處可逃了。他小心翼翼在寬廣的調車場繞了一圈.最後總算發現那節火車。從距離五0公尺以外的貨車暗處認出長禮服男子就站在乘車口之後,威魯暫且撤退。他把錢包藏在閣樓間的隱密處,到專門提供勞工與窮學生餐點的經濟餐館填飽肚子,一邊等待太陽完全下山。六點三0分,威魯第三度現身于調車場,他以為自己應該會覺得有點畏縮,不過興奮的心情似乎比較重,所以一點也不覺得可怕。他輕手輕腳藏身在貨車陰暗處,遠眺目標中的車廂內燃起昏暗的燈火,窗簾被拉開,因此可以清楚望見包廂內部,也因此威魯的目光准確抓住了包廂乘客的身影。是那名少女!與威魯同年齡或者再小一歲。威魯的雙眼完全肯定她與相片中的少女是同一人。她在相片裡被單一的泛黃色彩鎖住,然而現在卻存在于這個現實世界的自然色彩之中。她坐在窗邊,目光隨意瀏覽。心髒開始在威魯的胸口跳起舞來,而且是相當快速又強力的節奏,隨著血液循環加速,體溫也開始上升。威魯一邊調整呼吸一邊觀察,這時少女從窗邊站起身來,以為她拿起看似毛毯的布料是要遮住車窗,不料傳來一個鈍響,窗玻璃應聲碎裂,看來她是把一個類似花瓶的重物砸在毛毯上,毛毯跟著飛出車窗外落到地上。這一瞬間,威魯的思緒凍結了,平日的矯健被剝奪一空。等他想明白眼前看到的情景所代表的含意時,少女已經跳出車窗,拼命奔跑。她是不是哪裡受傷了?威魯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因為少女的動作宛如斷了線的傀儡娃娃一般生硬笨拙,下一刻他立即明白其中的原因。少女的左手與左腳被鎖鏈拷住,由于長度不夠,跑步時只有同手同腳才能前進。頓時怒氣在威魯的體內爆發,拿鐵鏈拷住一個女孩子的家夥絕對是個壞蛋。他一時忘了目前情況危險與必須小心謹慎,倏地從貨運車廂的陰暗處跑出來。「等我一下,我馬上去幫你!」他喊道,腳下濺起紅土往少女所在的方向奔去。不,應該說正當他准備跑過去之際,一個充滿壓倒性重量感的物體直逼而來。月光受到反射,冷硬光滑的物體閃爍著青白色的光亮往威魯撲來。當閃光削過威魯頭頂,他才認清那是異常銳利的騎兵專用單刀。雖然機警地躲開,威魯的內心早巳刮起了冬天的寒風,對方擺明了想殺他,威魯從對方默不作聲瞅著自己的目光看出這一點。軍刀握在巨掌中,手掌連到粗壯的手臂,往上接到厚實的肩膀,頭的位置比法萊抄警長高出—0公分以上的巨人揮動軍刀如同馬鞭一般輕松自如,准備把威魯的頭當成甜瓜一樣剁碎。狂風般的斬擊再度襲來,威魯用力往後一跳,著地的同時以鞋頭踢起紅土,紅土濺到巨人臉上,但巨人不以為意地重重踏出一步,猛力揮出軍刀。威魯勉強閃過,卻也明白自己的無能為力,不僅救不了少女,甚至連要救自己都比登天還難。威魯再次以鞋頭踢起紅土,這次有一小部分飛進巨人眼裡。軍刀停止回旋,巨人只手覆臉,威魯趁機翻了一圈逃出生天。無力感的折磨與懊惱的情緒沖撞著心髒,但現在除了逃走別無它法。一個聲音叫喚著伫立原地不動的巨人,他收起軍刀,轉身折回。一對身著長禮服的男女正站在車廂乘車口交談。「逃掉了?」「身手敏捷的小鬼。」「你讓他逃掉了?」女子咄咄逼問,男子明顯露出不悅與不甘的表情,卻不得不點頭。「格茲這家夥,有能力赤手空拳勒死一頭熊,居然沒辦法撕裂一只小老鼠。」「就當格茲只有這般能耐吧,我倒要問你,格茲剛剛賣力捉老鼠時,你在做甚麼?」男子聽了這句質問,刻意做出大感意外的神情。「真教我吃驚,你竟然把將軍跟士兵視為同—等級?」「你說誰是將軍?」「……反正沒事就好,沒有讓那個女孩逃走,而那個小鬼雖然跑掉,不過就算他說出去也不會有人相信他的。」女子語氣冷淡地打斷男子樂天的說詞。「我指的是你做了一件平白惹人注意的無聊舉動,你今天早上那個行動究竟是甚麼意思?這樣不就等于主動宣傳這裡很可疑。」男子以指尖撚著卷曲的小胡子,調整聲音與表情。「唉,沒甚麼好擔心的,這裡不是倫敦也不是巴黎,我也不認為這裡會有與福爾摩斯或羅蘋相抗衡的知名刑警,說穿了全是一群分辨不出槍聲跟雪崩聲的鄉巴佬。」「你可以瞧不起別人,但是別人沒有義務忍受你的批評,倫敦市警局(蘇格蘭警場)的刑警當中有不少人也是出身窮鄉僻壤,你最好不要忘了。」女子的指摘似乎是刺傷了男子精神層面的舊傷,他眯起雙眼,嘴角扭曲,女子無視對方表情的變化,語氣愈發嚴厲。「幹脆趁現在把話講清楚吧,丹曼先生,我是利己主義者,可以原諒自己的失敗,卻受不了別人的失敗,況且這次事情的主導權是掌握在我手上,而不是你。」男子無力反駁,勉強擠出僵硬的笑臉,輕輕舉起雙手。「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覺得我先前做事已經非常小心了,總之今後我會多加注意的。」「那就好,對我們彼此都好。」冷冷做下結語,女子以帶有韻律感的動作轉過身,男子目送她身披長禮服的背影離去,眼中燃著怨恨的火焰,看來要熄滅沒那麼容易。Ⅴ艾佛列特·法萊沙警長的辦公桌就位于市警局大樓二樓西側刑事組的一隅。警官們的職務劃分並不像倫敦市警局那樣清楚明確,法萊沙警長手邊的案件種類已經累積到六十項之多,其中還包括「惡意散播謠言與無端小題大作而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罪行。晚上七點剛過,這類嫌疑犯便沖進市警局,在樓下咆哮叫罵,腳步聲紊亂雜逐。法萊沙警長聞聲從樓梯井往下望,正好看見威魯雙臂被兩名警官鉗住,不停掙紮。「警長、請聽我說!」威魯擡頭認出警長,兩腳在半空拼命甩動。「我平常可以為了自己瞎扯,可是這次人命關天,我絕對不會說謊的!」威魯豁出去了,他只能來拜托法萊沙警長,如果無法取得警長的信任,威魯也無計可施。「好詞兒,聽了會讓人很想相信你。」警長做勢點頭,警官們帶著一臉老大不願意的表情,放開壓住威魯的手。「上樓來吧,威魯。」還不等警長說完,重獲自由的威魯立刻奔上二樓。警長泡了一杯濃濃的咖啡,把白鐵制的咖啡林遞給以炮彈般的速度與氣勢沖進刑警組辦公室的少年。「來,把話說清楚,冷靜一點。」「一群歹徒抓走一個女孩!」「哦?」「他們把她關在車廂,叫一個大塊頭拿軍刀監視她。」「哦噢,那個大塊頭有長角跟翅膀嗎?」「警長!」「抱歉,人命關天,請繼續。」威魯整理記憶努力說明,語間還很擔心那名少女不知會發生甚麼不測。這時他也老實招出扒走長禮服男子錢包的事情。警長愈聽表情愈顯嚴肅,當威魯把話說完,警長整個人已經陷入凝重的沈思。警長正要開口說話之際,一陣倉促的腳步聲接近,身著筆挺制服的警官恭敬行禮。「警長,局長找你。」這是相當罕見的,區區一介警長居然能得得到局長親自點名。警長側著頭,他當然不能拒絕,當下對威魯抛下一句:「等我下,我馬上回來。」便前往局長辦公室。現任市警局局長年約五0,有著蛋型的臉與身體,當然是不可能盯上法萊沙警長,區區一介青年警長在市警局局長眼中僅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會引起注意反而奇怪。因此法萊沙警長不自覺內心做好防備,可惜他的想象力不夠,完全沒想到這事會與威魯日擊的事件有關。警長按慣例行禮之後,默默等待局長的第一句話。「聽說有個不負責任的市民跑到你那裡大鬧。」局長牽動臉上讓人聯想到橫擺的長方形胡髭說道。「是,的確鬧得很大,但不算不負責任,事情是這樣的……」警長簡短說明,可是局長似乎一點感覺也沒有。「聽說這個名叫威魯的小孩是個聲名狼藉的流浪孤兒,這種貨色說的話值得相信嗎?」想不到威魯還蠻有名的,連高高在上的市警局局長大人也知道,法菜沙警長暗地如此思忖,表面仍然繼續默不作聲等待局長的下一步反應。只見局長不耐煩地下令:快快把他趕出市警局,念在他年紀小,不以散播謠言罪定罪,再不聽話就直接送少年感化院,我才要說你,你現在還有閑情理會流浪孤兒的胡言亂語嗎!」「不,我忙得不可開交。」警長從局長辦公室告退之後,就把威魯趕出市警局,不過他自己也跟著離開市警局,兩人肩並肩走在夜路,威魯將不滿丟向位于高處的警長耳朵。「你不是說會相信我嗎?為甚麼還要這樣對我?」「我相信啊。」警長的語氣算不上一般大人位于高處安撫小孩的典型範例,因為他自己也疑問重重,市警局局長的態度略顯失當,讓他也不禁開始懷疑緊閉的門扉另一端隱藏了甚麼秘密。「怎麼辦?那個女孩子會被殺掉的。」「不,我覺得暫時不必擔心,那個女孩恐怕是人質之類的,必須留她活口,比較需要擔心的是她會被帶往其它地方。」「這麼一來,要趕快救她出來才行。」威魯才熱切提議,臉上便被打上一條光帶。警長錯愕地錯肩轉過頭,目光隨即捕捉到兩顆地面而來的光球,是汽車的車頭燈。警長機警地把威魯的身體撞開,自己則往後仰倒向反方向,凶狠的黑色人工猛獸穿過兩人中間,准備輾斃威魯與警長。警長在路面翻轉修長的身軀,掉轉方向的汽車輪胎在他鼻頭前方三公分半的位置掠過。警長發出低沈的咒罵聲,掏出西裝內袋的制式手槍。然而還不等他擺好射擊姿勢,箱型車再度沖來,輪胎軋軋作響,車內傳來槍聲。在路面跳起的子彈劃破子夜氣,耳邊傳來玻璃碎裂聲,並重疊另一聲槍響,是警長開槍反擊。又是玻璃碎裂聲,黑色的人工猛獸看來搖搖晃晃,由于人們被這個意外嚇到,紛紛聚上前,汽車猛然掉轉車頭奔馳而去。「威魯你設事吧?!」「嗯,還好。」威魯一邊站起身,一邊盡可能精神奕奕回答警長,同時他確實體會了一點:看樣子自己已經開啓了一道通往與和平甯靜無緣的世界的門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