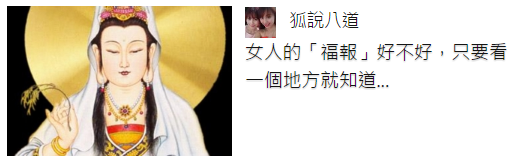一位朋友與一位台商老總談業務,午餐時在酒店點了菜品,該老總指著雅座中的酒水說:「請隨意飲用,我們不勸酒。」朋友知道很多南方商人商務會餐時絕不飲酒,也客隨主便,草草用飯。

翻拍微信下同
席間酒店服務生端來一道特色菜,那位老總禮貌地說:「謝謝,我們不需要菜了。」服務生解釋說這道菜是酒店免費贈送的,那老總依然微笑回答說:「免費的我們也不需要,因為吃不了,浪費。」飯畢,老總將吃剩下的菜打了包,驅車載著朋友出了酒店。
一路上,那位老總將車子開得很慢,四下里打量著什麼。朋友正納悶時,老總停下車子,拿了打包的食物,下車走到一位乞丐跟前,雙手將那包食物遞給乞丐。朋友看到那位老總雙手遞食物給乞丐的一剎那,差一點就熱淚奔流。
二
一次,葉淑穗和朋友一起拜訪周作人。他們走到後院最後一排房子的第一間,輕輕地敲了幾下門,門開了。開門的是一位戴著眼鏡、中等身材、長圓臉、留著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他們推斷這位老人可能就是周作人,便說明了來意。可那位老人一聽要找周作人,就趕緊說「周作人住在後面」。於是,葉淑穗和友人就往後面走,再敲門,出來的人回答說周作人就住在前面這排房子的第一間。他們只得轉回身再敲那個門,來開門的還是剛才那位老人,說他自己就是周作人,不同的是,他穿上了整齊的上衣。
三
夏衍臨終前,感到十分難受。秘書說:「我去叫大夫。」正在他開門欲出時,夏衍突然睜開眼睛,艱難地說:「不是叫,是請。」隨後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
四
顧頡剛有口吃,再加上濃重的蘇州口音,說話時很多人都不易聽懂。一年,顧頡剛因病從北大休學回家,同寢室的室友不遠千里坐火車送他回蘇州。室友們憂心顧頡剛的病,因而情緒並不高。在車廂裡,大家顯得十分沉悶,都端坐在那兒閉目養神。顧頡剛為了打破沉悶,率先找人說話。
顧頡剛把目光投向了鄰座一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身上,主動和對方打招呼:「你好,你也……是……是去蘇州的嗎?」年輕人轉過臉看著顧頡剛,卻沒有說話,只是微笑著點點頭。
「出去……求學的?」顧頡剛繼續找話。年輕人仍是微笑著點點頭。一時間,兩個人的談話因為一個人的不配合而陷入了僵局。「你什麼……時候……到終點站呢?」顧頡剛不甘心受此冷遇,繼續追問著。年輕人依舊沉默不語。
而這時,坐在顧頡剛不遠處的一位室友看不過去了,生氣地責問道:「你這個人怎麼回事?沒聽見他正和你說話嗎?」年輕人沒有理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微笑著,顧頡剛伸手示意室友不要為難對方。室友見狀,便不再理這個只會點頭微笑的木疙瘩,而是轉過身和顧頡剛聊起來。
馮友蘭
當他們快到上海站準備下車的時候,顧頡剛突然發現那個年輕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了,只留下果盤下壓著的一張字條,那是年輕人走時留下的:「兄弟,我叫馮友蘭。很抱歉我剛才的所作所為。我也是一個口吃病患者,而且是越急越說不出話來。我之所以沒有和你搭話,是因為我不想讓你誤解,以為我在嘲笑你。」
馮友蘭的尊重就在於「不說話」,而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絞刑架的時候,不經意間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下意識地說了一聲「對不起」,這是一種極其高貴的尊重,讓每個人都肅然起敬。
五
67歲的瑪格麗塔 ‧ 溫貝里是瑞典一名退休的臨床醫學家,住在首都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松德比貝里。一天早上,溫貝里收到郵局送來的一張請柬,邀請她參加政府舉辦的一場以環境為主題的晚宴。
溫貝里有些疑惑,自己只是一名醫務工作者,跟環境保護幾乎沒有什麼關聯,為什麼會被邀請呢?溫貝里將請柬仔仔細細看了好幾遍,確認上面寫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後,放下心來:「看上去沒什麼不對的,我想我應該去。」於是,溫貝里滿心歡喜地挑選了一套只有出席重大活動時才穿的套裝,高高興興地赴宴去了。
趕到現場,溫貝里不由得吃了一驚:參加晚宴的竟然都是政府高級官員。其中就有環境大臣萊娜 ‧ 埃克,他們曾經在其他活動中見過面。看到溫貝里後,埃克先是一愣,然後馬上向她報以最真摯的笑容:「歡迎你,溫貝里太太。」接著熱情地將溫貝里帶到相應的座位上。溫貝里和政府要員們一起進餐,並聆聽了他們對環境問題的看法和建議。
宴會結束後的集體照。右起第一位即平民溫貝里
宴會結束後,按慣例要拍照留念,埃克邀請溫貝里坐在第一排。就這樣,溫貝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幾天後,溫貝里瀏覽報紙時,看到了自己參加晚宴的合影和一則新聞報導:「政府宴請送錯請柬,平民赴約受到款待。」
原來,環境大臣埃克本來邀請的是前任農業大臣瑪格麗塔 ‧ 溫貝里,由於工作人員的失誤,把請柬錯送到和農業大臣同名同姓的平民溫貝里手中。對此,埃克表示:「不管她是誰,只要來參加宴會,就應該受到尊重和禮遇。」
看到這裡,溫貝里不由得心頭一熱,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埃克明知她是一個「冒牌貨」,非但沒有當場揭穿,反而給予了她大臣一樣規格的禮遇,這樣不動聲色的尊重足以令她欣慰一生。
尊重的最高境界不是體現在轟轟烈烈的大事之中。有時候,越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越是不經意的自然流露,越發見得尊重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