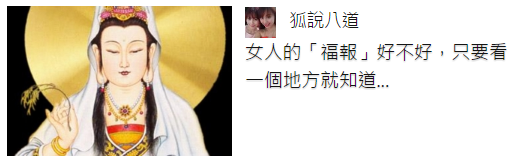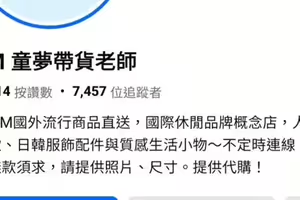大約是在一個冬天的清晨,才六點出頭,天都還沒亮,太陽還賴在雲層後,一個女孩推開了面包店的門,而我正在伸懶腰。
彎折到後背的頭連忙就彈了回來,挺直腰杆,擺出職業性的笑容。
“早上好,小姐。想買點什麼呢?”我知道,這個問題對於一個剛進門的客人來說太過為難,連一圈都沒繞過,怎麼知道有什麼貨色呢,但是,我這樣做的理由又很正當,作為服務員,就應該這樣,而且我知道躲在廚房門後的老板正豎起耳朵聽著呢。
她隻抬頭看了我一眼,就低下頭去,小聲地說:“我先看一下。”
“好的。”我回答,而後就跟在她屁股後面,一臉關心。
女孩臉色蒼白,墨綠色的高領毛衣遮住了她的脖子,過長的手袖沒過了她的手掌,隻看到她袖角處有手指的抓痕,外面很冷吧,我想。
她走到面包櫃前,里面是新鮮出爐的烘培面包,有香腸包、肉鬆玉米包、甜甜圈、菠蘿油、牛角包、芝士雞扒包、以及包裝好的公司三文治。她低頭靠近玻璃,似乎想要看透所有的面包,很難選擇吧,我想。
這時,廚房內突然傳來一聲咳嗽。
我回過神來,立即彎下腰,問:“這里的面包都剛出爐的,很新鮮,小姐,想要吃什麼呢?我個人推薦這款芝士雞扒包,一向都很受客人喜歡喔。”其實它的價格是最貴的,還有,這擺著的明天就過期了。
女孩突然就抬起頭,差點就撞到我的鼻子,她還是輕聲說,“我再看一下。”
“好的。”我回答,還是跟在她的屁股後面,一臉的耐心。
接著她來到了包裝面包區,竹籃里裝滿了紅豆包、蟲蟲包、奶油包、小年糕和沙琪瑪各類的小甜點。她低頭看,挺直的鼻梁骨動了幾下,如同抖動翅膀的飛蛾。這姑娘有選擇困難症,我想。
這時,廚房傳來挪動桌子的聲音,還有勺子敲擊玻璃的聲音。
介紹的時候,下意識地堵住鼻腔的上部,發出類似於台灣腔的鼻音。“小姐,這里的小甜點每樣都很好吃喔,像這款蟲蟲包,里面是綿軟的奶油,一口吃下去就融化在嘴里,您可以試一下喔。”同樣也是快過期食物。
女孩終於抬起頭,看向我,說,“不用了,我自己會選。”
這一記眼神里有驅逐,有生氣的意思,還有一絲閃爍的狡黠。
真是托了廚房那位的福,我快要成功地逼走一位客人。
她還是沒有選到面包,兩手空空地又來到了蛋糕區,冷凍的玻璃面在她靠近後,生起了一層水霧。她的下巴向前傾,這讓我想起了街尾那戶八十歲的老奶奶,她吃東西的時候就這樣,兩片嘴唇用力地磨碎她媳婦為她準備的瘦肉粥。
接下來的這一幕讓我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女孩的鼻孔動了幾下,像是在吸食什麼,透過玻璃面我看到了她眼里滿足的笑意。
這姑娘……該不會是鬼吧,我想。
沒等廚房鬧出點聲響,我就趕緊轉身走進了廚房,推開門,翹著二郎腿的老板正嘟起嘴唇,快要從那個孔里吹出蕭。
我連忙掩上門,用一手指堵住了那個孔,而那隻手前幾秒還撓過我的屁股。
老板睜大了眼睛,隨即憤怒,張嘴就想質問我在干嘛。
不想打草驚蛇,我來不及多想,就整隻手蓋住了老板的嘴巴,並且在老板耳邊低聲說:“老板,不好了,外面有情況。”老板右嘴角下有一顆痣,痣上有毛,毛穿過了我的手指縫隙,很癢。
老板立即推開了我,用手背不停地抹他的嘴唇,一臉嫌棄地看向我。
“你小子,手怎麼那麼鹹。看把你緊張的,什麼事啊?”說完他伸出另一隻手把剛才歪掉的金表扶正了過來,那是一隻純金表,圓圈邊上都鑲滿了鑽石,老板很愛惜它,兜里常備著一塊絲綢布用來擦拭它。
我一副大事不好的表情,輕捂著嘴巴,又看了一眼外頭,“老板,外面有一個女的,有點古怪,我在想,是不是那些不干淨的東西。”
老板一聽,腳尖都踮起來,用嘴型在說,真的假的。
我用力地點點頭,下巴指向外頭,一臉為難地向老板眨眼。
老板嘖了一聲,輕輕地拉開廚房的窗,就一條線的縫隙,他湊上前,不到三秒,就轉過頭深呼吸了幾口,跟我說:“真的假的。誒,是不是你小子神經過敏,人家好好一個人被你說成鬼啦。這大白天的哪來的鬼。”
我們齊刷刷地看向窗外,一片漆黑,霧氣讓街道顯得特別迷幻。
於是我接著說。
“才不是呢,老板,我小時候遇見過,對那種東西特別敏感,而且那姑娘壓根就不拿面包,我就沒看見過她的手,就一直在那里吸,跟電影里演的鬼一樣,吃東西是用吸的,我想,八九不離十了。而且女鬼特別難纏,我們村里就曾經有一戶人,因為兒子不孝,拋下母親和他奶奶不顧,發財了也不曾想過她們,那兩人在一次寒潮里雙雙凍死了,冤魂便找上了那兒子,每天夜里追問他為什麼不來找她們,兒子最後就進了精神病院,每天都在說道歉,至今都還是傻的。”
說到後面,老板渾身都打了個顫,他揮手示意我別再說了。
“別說了,別說了。”他停了下來,捏著眉宇之間的那塊肉,想起了一些事,似乎很痛苦。
“等一會兒吧,差不多天亮了,會走的,會走的。”他雙手合十,用力地握住手掌,後面說的那兩句更像是在安慰他自己。
我舒開眉頭,雙手插在胳肢窩下,靠著桌子,不動聲色地鬆了一口氣。
大概半小時過去了,天亮了,雲霧散開,太陽張開嘴巴,射出光芒。外頭也安靜下來了。
我打了個哈欠,甩了甩腦門前的劉海,對還在燒香念經文的老板說:“老板,好像走了,沒聲音了。”
老板張開眼睛,把手中的三支蠟燭插在了他剛才做好的臨時供奉台里,就是一個拿來打奶油的盤子,里頭裝滿了面粉。
“好,你出去看看。”
“不一起嗎?老板,我還是怕。”我說。
老板果斷地搖頭,非常地用力,我深怕他會不會就把腦袋給甩了出去。
我捂著胸口,連深呼吸幾口,用蝸牛挪動的速度打開了廚房門,探出頭張望後,就敞開了廚房門,“老板,走掉啦!”
老板呼出一口長長的氣,對著臨時供奉台,頻頻鞠躬,念叨著感謝文。
“謝謝您,大人不記小人過,細路仔不識世界,謝謝,謝謝。”
我走進店里,發現每個籃子都空出幾塊。
我大喊道:“老板,不好啦!少了好多東西,面包啊,牛奶,還有口香糖,還有咱們店里附送的周年情侶杯。”
老板立即從廚房里出,無奈地說:“算啦!反正面包那些好多都是放了幾天快壞的,給她拿了也沒事。都是些便宜的東西。走了就好。”他手捂著金表,幾根手指忽上忽下地輕拍著。
“可是,老板,她拿的都是今天進貨的批次,我天,這鬼也太精明了吧。”
老板雖有些不高興,還是揮手說:“算啦,算啦,把昨天的面包拿出來填上吧。走了就好,走了就好。”後面那兩句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他走到收銀台處,說:“錢呢?錢沒少吧。”拉開收銀櫃後,清點了金額,沒有少。老板指著擺滿了口香糖和紙巾一類百貨的那個角落說,“等會兒你把這里收拾出來,我去把家里的那尊佛請出來,擺到這里來,就不怕了。”
我應聲說好。
我把籃子里空出來的地方再次填上面包,褲兜里傳來震動。
“忘記拿小年糕啦。”句子後面是一個委屈的表情。
我快速地打上幾個字——“沒事,反正監控壞著,明天再拿!你哥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