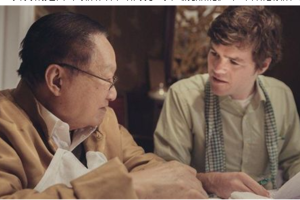燈花不堪剪
track 01
蘇紫慢悠悠地伸了白淨的五指,竟劃出個奇低的價錢。
“七文,多半個子兒不要。”
藥鋪掌櫃慍道:“多給個幾文會要你命麼?”
“會!”蘇紫答得乾脆,他拈了片獨活在燈下照,“看你這藥材,觸手粘膩顏色灰暗,說不定是假的,吃死人也未可知。”
作藥材的,最忌人辨真辨假,老闆立時黑了臉罵道:“有種你不要買!”
蘇紫遇強則弱,反忝笑道:“我自是沒種的,今兒個買不到我還不走了。”
老闆見他根本是個無賴,也只得自認倒楣。七個銅子兒七貼藥,包了扔到他面前。
蘇紫正付了錢,鋪外進來兩三個大漢,後頭跟著個娘姨,怒衝衝地指認道:“就是他!方才在街上順了我錢的賊骨頭!”
蘇紫看清來人,立刻抓了藥包在手,卻還嘴硬道:“我當哪位金主兒,原是大庭廣眾下拿胸脯兒蹭我的大娘。”
兩個大漢與那娘姨在一個府上做事,平素也知道這女人的秉性,當裡下哭笑不得。立時被娘姨狠命捶了兩下,喚狗似地呼喝著他們給蘇紫一頓教訓。
蘇紫肢體瘦小,身量不足六尺,自不是大漢的對手,兩三下便挨了拳腳。他本就吃得不足,又一氣兒趕了好些路。略撐了會兒便抱著藥包逃跑,出門時還不忘順了一袋桔梗種子,氣得藥鋪老闆跳腳。
幾個人追出鋪子,卻哪裡還見蘇紫的人影?一通亂找之後依舊回到藥鋪門口,卻見到大隊戎裝的兵士立著,中央一把交椅,坐著個雕氅鱗衣的官吏。
掌櫃的心裡怯了幾分,賠笑上前,卻被詢問是否有人前來買過大補的傷藥。
“回官爺的話。”掌櫃面露難色,“猛的藥倒沒買過,尋常傷藥倒買了十幾貼。”
那官吏問:“最近一次是何人,你可認識?”
掌櫃答:“草民不認識,言行舉止卻是個無賴混混的模樣。”
官吏有些疑惑,又問道:“可曾有衣著華麗之人,或是箭衣武人來你這裡買藥?”
掌櫃努力想了想,終是搖頭。
邊上文士模樣的人提醒道:“他們也有可能改扮成了布衣,大人不妨問問具體長相。”
官吏點頭,掌櫃眨了眨眼道:“那人身不到六尺,長得倒眉清目秀,卻嫌陰柔太過,對了,額上一道寸余的白疤。”
文士低聲道:“公子晗的一等門客裡未見如此相貌之人。”
官吏點頭起身上馬,兵士們便又整了隊形出發。留下掌櫃與出來看熱鬧的一干閒人。
“今兒個唱得可是哪出啊?”
“章國君薨,留在我國都城的質子晗,昨夜潛逃了。”
“世子,蘇紫此人您該捨得!”
燈光下,李冉虯空首在地,痛陳道:“家國興亡之際,男寵隨身,其非徒留後世恥笑?”
“阿紫非是男寵。”公子晗收了書卷在手,冠玉的面龐在燈下熠熠生輝,“他乃我門下食客,患難時又誓死相隨,我棄有其之而去的道理。只怕依了李將之所言,更加落人口實。”
李冉虯道:“公子此番回章,便是要承襲王位,迎娶妃後。蘇紫留在您身邊也是尷尬,不如就此放他自由。”
公子晗卻笑道:“此番回章國,第一要務為聯合各小國勢力共擊錢國。蘇紫之姊曾為郭國公寵妃祥夫人婢女,日後必能建立奇功。”
李冉虯不屑道:“蘇紫淪落風塵多年,舌燦蓮花,這事公子如何信得?”
公子晗笑道:“清倌尚不算風塵,至於舌燦蓮花,倒真作得說客豈不更好?”
李冉虯蹙眉道:“蘇紫生性散漫,刻薄小氣,不服圭臬,如何用得?此刻又不知去了何處,留在身邊徒增危險!”
公子晗道:“他做事,自然有向我報備。這事我有取捨,李將不必多言。”
李冉虯說不過他,只是依舊跪在地上。不多時耳邊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李冉虯立刻捉刀回防,身後卻是直通到地面的井壁,從上面沿著繩梯下來一個青年。
清秀的臉龐,額角卻留一道白疤。正是蘇紫。
“就知道是你。我連燈都不滅了。”公子晗笑道。
紫蘇一手提著藥包穩穩地下到井底的岩石上,趟水入了耳洞,作揖道:“勞煩公子替食客操心了。”
正說著。井沿上被人用木桶重重地被人磕了三下。原是搜查的人來了,公子晗忙熄了燈燭。三人靜處了約一燭香的時間,又聽三聲悶響,才道危機解除。
過了一會又點上燈,蘇紫已窩進了公子晗懷裡。世子竟親自以指腹替他按摩著太陽穴,李冉虯看不下這等親昵之事,心裡正歎氣,忽見紫蘇抬頭,將七貼藥擺到了案幾上。
“李大人,這是你的傷藥,我怕留下線索,只能要了較溫和的。恢復得倒不慢,只是不太鎮得住痛就是了。”
李冉虯見他竟是替自己抓藥去的,面上陣青陣紅煞是好看。正不知所措中,井上又下來了一個白衣儒士。
track 02
儒士是地上草廬的主人,也是章國暗樁,他送上飛鴿書信。公子晗展開紙卷,上面略陳了章國的時局;重要的是三日後,章國的 十位死士將潛至錢國邊境驛站,將世子護送回章國。
“驛站距此處僅六十裡,中間還有另一處暗樁可供世子歇腳,回國之事指日可待。”白衣儒士如此解釋,又看見了蘇紫買來的藥,“剛才軍士過來搜查,看誰家買了傷藥。幸虧蘇公子親自買了,要我去的話怕是已經惹了麻煩上頭。”
蘇紫聞言,嬉笑著吐了吐舌頭。
一邊的李冉虯只當儒士阿諛迎逢,心中益發擁堵,乾脆上井去透氣。少時儒士也離開了,蘇紫照舊軟綿綿地倒回公子晗懷裡,由他當暖爐般抱著繼續閱讀信箋。
過了會兒,兩人似是都有些倦意,蘇紫正起身,肚子裡卻一陣骨碌,正是餓極。忙要掩飾,卻被公子晗用手貼在了肚子上。
“怎麼是癟的呢?”
時值隆冬,窮鄉僻壤本就物源匱乏,所有食物必須保證世子需要,李虯髯身為護衛必須補足體力,剩下的也就寥寥無幾。
蘇紫卻毫不在乎道:“鼓著的是蛤蟆!食客這肚子吃飽了也會叫。公子要是被食客的肚子騙了,如後如何在朝堂上明辨忠奸?”
公子晗收了書卷,溫柔地笑道:“就你嘴滑,比菜裡還多油。”
說著便俯身親他的唇,又從懷裡取了個小瓶,倒出兩枚小丸來。
“還剩幾枚大補丹,雖不能填饑,卻能提攜精神,我看你有些萎靡,白日裡趕路不要掉隊才好。”說著,硬塞到蘇紫手心。
青年拿了藥丸在手,嘖道:“如此精貴的東西,你給我,我還捨不得吃。合著賣了錢,能吃好幾頓……”
話音未落,公子晗突然銜了一粒吻上他的嘴唇,以舌尖推入他喉中,又捏著他的頸項強迫吞下。
蘇紫初時肉痛,眼中繼而有光流動,他抿了抿嘴角,最終幻化出了一個霧裡花開般的笑容。
第二天醒早離了儒士家,三人騎馬照小路向東邊趕去。追捕之人可能已趕到前面,一路上倒也無風無浪。只是向晚落了冬雨,三人皆淋濕了。蘇紫腹中空得發痛,落在最後,偷偷抖得如秋葉一般。
所幸暗樁住處不難尋找,急雨襲來前三人便被迎進了屋子。這一家暫且以打獵為生,食物倒比鎮上富足。蘇紫最後一個擦乾了出來,還能分到個碩大的鹿腿。
公子晗與暗樁進了密室,李冉虯在廄裡喂馬,蘇紫一人坐在四面透風的廳上,餓到極致,反沒了胃口。只是吃了個半飽,便拿匕首細細剔肉,包到一塊乾淨手絹裡。
他正剔得起勁,李冉虯突然推門叫他出來。雖然情知沒有好事,蘇紫卻依舊將匕首的兩面舔乾淨,又把手帕紮好了,才走出門去。
屋外,冬雨傾盆,簷前掛了雨簾,聲音隆隆。
李冉虯立在陰暗裡,看不清表情,蘇紫只聽見他問道:“早上你往馬上裝的那個袋子是什麼?”
蘇紫回答:“桔梗種子,幫將軍抓藥時順來的。”他將抓藥二字著重,頓了頓又道,“暗樁家的物品,食客一向來不曾染指。將軍放心。”
李冉虯似是理虧,換了話題道:“知不知道你已經是一個累贅?”
蘇紫故作驚訝道:“食客一路未曾拖累行程,未曾勞動世子與將軍費神。食物藥材,食客能出力的地方從不偷懶,何來累贅之說?”
李冉虯突然上前一把握了他的手,略微扯動,青年便齜牙咧嘴地蹲了下來。李冉虯冷笑道:“你在質子府上時便多病。世子視而不見,你自己也該明白。貪生怕死乃是小人所為。”
“食客是小人!”蘇紫忍痛道,“雞鳴狗盜之輩或許比我更有用處。然而小人也有義氣,我雖曾以身取悅公子,然而公子卻並不以男妾對待,反奉我為食客。此等恩德,食客自當圖報!”
李冉虯道:“現在離開,便是最好的報答!”
聽了這話,蘇紫乾脆坐到地上:“等到食客真的走不動的那天,自當主動請辭,然而一日能夠跟上,便一日不離開世子身旁!”
track 03
雨停了。
公子晗展了花箋,草擬歸國後連縱的檄文。天冷,邊上蘇紫一遍遍地研了墨,又塞了湯婆子到公子懷裡,煨在邊上看他寫字。
蘇紫並不識字,卻懂得文字的美妙。公子晗寫了多久,他便看了多久。
月色薄而亮的,像貝裡通透的珍珠色,柔柔地刷了一層在窗櫺上。夜見深了,文思便逐漸凝滯。洋灑的初稿落到地上的時候,男人不禁伏案入寐。
蘇紫癡癡地望著公子晗,流連在那儒雅英俊的面龐。這張他所迷戀的容顏,不知還能再注視多久?
依照自己的體力,日子其實是掐著算好了的,堪堪能陪公子行到錢國邊境。若明日順利與死士匯合,便依舊有望隨公子回去章國;若遭逢變故,就真不能再做那個“拖油瓶”了。
他怏怏地想著,胸中寒氣猛地糾結,忙伏到地上,用力壓住了咳嗽聲。帕裡的鹿肉從袖口掉了出來,落幾片在地上。他心疼地撿起來吹乾淨灰塵,無聲念著“吃了沒病”,都送入嘴裡。
這才幾個時辰,竟已嘗出了酸味。
寂靜的夜裡,蘇紫趴在地上咀嚼又咳嗽,抬起頭來滿眼是淚,剛吸了下鼻子,案上人便在夢中“嗯”了聲,他忙抹了臉侍在一邊。
燈芯長了,燒焦的地方縮成一團。待壓住了火苗,便聽見“啵”的一聲,燈花炸開。整個屋子的光影便不住地抖,像是屋外有人跑動。如此兩三回,公子晗警醒了,揉著額頭又提起筆來苦思。
蘇紫勸他歇息,卻遭了拒絕,反而被打發去歇息。他乖覺地退到外間簾後,隔縫觀察里間的狀況。直等公子晗又漸漸僕到案上,才偷偷矮了身子潛回他身邊。卻又不敢驚擾,於是傻傻地拿了剪子坐在案邊,拿著剪子挑剪燒焦的燈芯。
極小心、極仔細的,生怕驚擾了亮光,變出什麼古怪的影子來。那白蘭花般的五指,如此接近了火,仿佛下一刻就會燒溶,化作一滴淚。
這燈花,剪了一夜。
“本就不是多重的東西。”蘇紫笑道,將種子帶系到鞍上,“且不是我馱著。一點都不礙事……”,正說著,突然又伏在馬背上,止不住地咳。
“怎麼愈發厲害了?”公子心疼。李冉虯聽見,則更黑了臉色。
蘇紫搖頭:“許是昨天淋了點雨,清咳不防事。”
昨夜落雨耽擱了些行程,今日向晚方能到達驛站。所幸這一路荒郊野外,並無錢國所設哨卡,但若是過了客棧,情況便又未可知。
三人前後在一丈寬的泥徑上趕路,地勢逐漸起了,進入山坡,兩旁都是數丈的土崖,因昨夜的暴雨而滾落不少山石,又有不坑窪足了水,看不出深淺。
李冉虯正提及路況險惡,要二人多加留意。蘇紫不諳禦馬之道,稍不留神,胯下青馬便一個趔趄,竟就伏在了泥地上。公子晗眼疾手快拉了蘇紫,蘇紫則拽了桔梗袋子。兩人同時被青馬濺了一身的泥漿。
李冉虯下馬察看之後道:“馬腿折了,不能再騎。”完了又瞪蘇紫一眼。
公子晗歎道:“路上泥濘顛簸,怪不得阿紫。倒可惜了這匹馬。”又拉了蘇紫上馬,“你本就輕,與我共乘該不是問題。”
說罷,以眼神堵了李冉虯的口。三人兩騎依舊上路。卻聽聞身後馬嘶陣陣,回頭看去,竟是青馬跛著傷腿跟了上來。
“畜牲尤忠心若此,實讓人感歎。”公子晗嗟道,“如此跟著,卻更是個麻煩。”
蘇紫聞言,心中突地一跳。
他又聽公子晗對李冉虯道:“且隨我來。”
track 04
兩騎前行,青馬頑強地跟在後面。前面是三叉口,應左行,公子晗卻偏向右走,那青馬自然跟上,如此十丈之後二人翻身下馬,那青馬也極通靈性地跪倒。蘇紫站在公子晗身邊,已隱約覺察了他的用意。
公子晗向李冉虯伸手:“劍來。”
李冉虯恍然道:“世子,請讓我來!”
公子晗搖頭,依舊道:“劍來。”
李冉虯無奈,奉了劍。只見公子晗仗劍在手,躬身溫柔撫摸青馬的鬃毛,貼近它耳邊喃喃細語。突然間銀光一閃,手起刀落間馬血噴薄而出。三人略略避開,公子晗目光溫柔地看著青馬漸漸停止了掙扎。
腥甜的血氣撲面而來,蘇紫揪緊了衣領。面前是馬血的微熱,身後卻是荒野的冰涼。
客棧立在野地的岔路口,不過一間大屋,前面掛了幌子後面加了馬廄。因為離開官道太遠,自然沒多少人煙,小二搭著布巾立在土坡上,遠見了客人,立刻跑回客棧報信。
飛鴿書信上原說好的,若死士先趕到客棧,則將頂替客棧全員。公子晗只須與掌櫃以暗語聯絡。
然而真正到了掌櫃面前,公子晗便明白事情未必順遂。
那是一位四五十歲的男人,抬眼皮看了來人,緩慢問道:“三位打尖住店?”
李冉虯唯恐他是死士易容,依舊拿暗語來對:“天地人三間上房。”
那老頭沒多餘的反應,甚至不見笑容,只伸手到架子上,摸了半天才找出三塊房板丟過來。公子晗默默看在眼裡,突然道:“肚子正饑,不如先用了晚膳再上樓去。”
說著就拉著蘇紫到堂裡坐了,李冉虯雖疑惑,卻也跟過去,三人點了飯菜,正等著,蘇紫突然說要尋茅廁,找了藉口便朝後堂而去。
公子的外袍沾了泥,隱約還有些馬血的斑點。路上又沒帶多少錢財,吃喝都甚為拘謹,蘇紫未曾見他如此落魄的樣子,心裡發酸。剛才遠遠見到一個商人打扮的從客房裡出來,手上綠油油一個碧玉扳指。想見是個富足之人,便要順些財物,至少吃一頓飽足。同樣也是為了殺一殺手癢,只怕日後入了章國,便要規矩做人了。
然而他才舔破窗紙瞧准了屋裡無人,身後便是一陣腳步聲,徑直朝這邊而來。蘇紫慌不擇路,竟關了門躲進里間的雪隱。布簾剛停了擺動,三四個人便推門進來。蘇紫只想等他們離開,卻不意聽見這樣一段對話。
“沒錯,正是畫上章國世子的模樣。”
“是否現在就下手?”
“且慢。探子說前來接應他的死士快到達客棧,正好來個一石二鳥。”
“我們的兵力足夠應付他們麼?”
“綽綽有餘。客棧裡已經做了佈置,只要他們進來,就別想出得去。”
蘇紫心驚,害怕之餘也明白該做什麼。雪隱東面有扇花窗。推開了便是野地。客房雖在一樓,屋子卻立在夯土坡上。從窗下跳下也足一丈有餘。然而他只期望不要被人發現,抬腳跨出,落到黃土地上滾了兩滾,也不知道哪裡更痛一些,只拼命咬了牙朝大堂跑去。
公子晗與李冉虯見他灰頭土臉,又從門外奔來,正在疑惑。忽聽蘇紫大聲笑道:“青馬,青馬跟來了!”
客棧裡的人一時不能明白話中的含義,而李冉虯卻已經微變了臉色。公子晗淡笑道:“那倒是好事。”二人起身便要走,剛走到門口,卻被小二攔了下來。
“質子晗。”掌櫃老頭皮笑肉不笑道,“這家客棧便是為你而開。”
話音未落,李冉虯已變了臉色,劍鞘未啟便直直擊向小二。公子晗則抓了蘇紫的手,疾步走出大堂。
這時,門口風塵僕僕的一騎人馬也恰好趕到。
track 05
打殺、求饒聲,與碎瓦、裂帛、斷木之聲混雜,蘇紫與公子晗被護在中央,李冉虯仗劍不離寸步,週邊死士衝突。然而錢國早得到線報,埋伏了精兵在周圍林間。縱然死士奮不顧身,寡不敵眾的局勢卻愈見明顯。
李冉虯見狀,搶來快馬與公子晗騎了,自己轉眼又奪了一匹便要帶頭突出重圍。只留蘇紫一人立在原地。
明白李冉虯是想要借機甩掉自己,蘇紫茫然地向四下裡看,自己卻要到哪裡去弄馬匹?正在猶豫,竟已被公子晗一把拉到馬上,坐在了他身後。
“捉緊我。”男人略微回頭與他說道,“此時此刻,我未必護得你周全。”
蘇紫點頭,忙抓緊了公子晗的衣袖,殘存的死士聚攏來護在四圍,兩騎迅速突圍, 只聽身後一聲喝令,“放箭!”
蘇紫未敢回頭去看,只聽見空中隱約一片振弦的輕響,然後是幾聲淒厲的叫喊,有人墜馬,緊接著他感到腰上一陣刺痛。不自覺伸手去摸,竟是支羽箭,沒入體內將近一寸。當下心涼了半截。
李冉虯見四周死士漸少了,忙退到公子晗馬後守備,愕然見到蘇紫背上的羽箭。那深度,怕是已經抵到脊柱,一旦感染腐敗,便極可能失去行動力。
他蹙眉,剛想開口說話,卻見蘇紫驀然回首,慘白的臉上掛著冷汗,將手指豎到灰敗的唇邊,竟是求他不要張揚。
依蘇紫現在的狀況,只需輕輕一扯就能拉下馬來。公子晗也沒有時機挽救。然而李冉虯也不知自己想的是怎樣,卻捉劍,將蘇紫背上的劍貼著衣裳斫去。
蘇紫乍時吃了一驚,忽而感激起來。李冉虯則黑沉著臉色,看著蘇紫悄悄轉動腰帶,把染血的一面轉纏到裡面,又撕了片衣袖墊在傷口上。
他明白這就是蘇紫對於傷口全部的處理,接下來的行程將更為艱難,不容任何人喘息。而蘇紫的離開,也只是時間問題。
為躲避錢國鷹犬的追緝,一行最終棄馬遁入了山林,換成徒步往邊境走去。
蘇紫背部中箭,卻因為箭鏑尚在體內的緣故,出血不多;加之連日奔波,衣上留下的醃臢倒也起了些掩飾。
然而每走一步,箭鏑便會在體內扭動一分,初時痛不可抑,慢慢感覺那一塊的肉都已經被攪爛了,疼痛也隨之麻痹,只是木然地隨著眾人前進。心中一片茫然,不知何時便會倒下。
公子晗對他依舊關懷,卻因為死士在場而指乎於禮節。多少次蘇紫疼得想要跪倒在地上,卻都被那雙溫暖的大手有意無意地一接,又都強忍了下去。
青馬之死,尤歷歷在目。
track 06
“無論如何,我李冉虯佩服你。”
夜裡,篝火外,李冉虯單膝點地,卻是對著蘇紫,“然而你也應該覺察,因你帶傷,眾人的腳程也被拖累。”
蘇紫點頭,一邊從衣裡取了殷紅的布條出來,又撕了另一邊衣袖換了,非是為了止血,事到如今,也只能盼著不要被別人發現而已。
他不無疲倦地垂著眼簾,點頭道:“端看明日……若還有氣力上路,也請李將軍通融一面。荒郊野嶺,雖沒有棺席,也該找個隱蔽之處躺下;我孑然一身,想來也無人祭拜,且讓我在做野鬼前再看幾眼世子,日後永駐這荒山深處,也有些可以懷念。”
那李冉虯雖是武人,聽了這話也有些動容,實在忍不下心來拒絕,糊塗地應了。蘇紫道了謝,也不急著回到正進食的人群裡,依舊掏出了那包鹿肉,在暗處一點點咀嚼。
天難遂人願,第二日熹微,蘇紫起了高熱,傷口感染的結果,便是難以掩飾的病態。他要抬手試額,渾身卻似散了架般,這氣力,恐怕是一去而不復返了。
邊上,死士正忙著熄滅篝火,蘇紫搖晃著起身,李冉虯見了便要不露痕跡地攙扶一把,卻被蘇紫刻意避開。回望的眼中幾分淒涼,竟然是無可奈何的作出了選擇。
果然,在眾人的注視中,蘇紫跪倒在公子晗面前。
“食客本無親人在外,更沒有做婢女的姐姐。路經此處,倒是想起了從前有個贖身的清倌朋友住在附近。”說著,還拿手胡亂指了個方向,“該是在那邊的山坡。”
公子晗似乎明白了幾分,卻未開口,只等他挑明用意。
蘇紫微咳了兩聲,繼續道:“食客生在錢國,雖為公子風采所折,然而故土之情不敢泯滅。昨夜思忖再三,還是決定投靠那位清倌朋友。”
說著,又小心地從懷中拿出一個手絹紮的小包裹來。
“這裡是公子的大補丹,蘇紫人微命輕,用了反覺得奢侈。不如留給公子,做個念想。”
公子晗沉著臉將包裹接過,上下打量著蘇紫如此明顯的病容,李冉虯幾乎就要以為他會看出些端倪,男人卻又沉吟不語,直到見了蘇紫手邊依舊放著那個不大的種子袋,突然歎息道:
“一袋桔梗尚捨不得丟棄,卻要如此輕易舍我而去麼?”
一語既出,蘇紫心中如遭痛擊,他苦笑道: “是……蘇紫貪生怕死…公子亦不必為蘇紫掛牽。公子的恩情,蘇紫唯有結草銜環以報。”
說著,不顧疼痛在地上磕了三個響頭。公子晗也只是沉著臉受了,儼然心傷內斂的模樣。
眾人之中,唯有李冉虯真正明白“結草銜環”的真意,本是看慣了死亡的,一時竟也酸楚至極。他本是至情至性之人,敬佩蘇紫的隱忍之餘,想起從前種種為難之舉動,自覺得面紅耳赤,卻始終還是以世子的安危為先,始終未置一詞。
track 07
這邊,蘇紫已經搖晃著起身,分明不大的桔梗袋子,卻逼得他要吃力地扛在肩頭,李冉虯心中刺痛,再看蘇紫後腰,已透出了巴掌大小,顏色分明的一塊殷紅。
任誰都難以視而不見。
死士中正有人催促應該上路,卻見公子晗疾步追到了蘇紫身後。李冉虯一陣錯訛,竟不知是喜是憂。卻輕聲喝住了蘇紫,看公子晗將一塊玉佩塞到他手中。
“晗這半生,只愛你一人。”
男人當著所有人,低頭吻向蘇紫項間。
蘇紫渾身輕顫,心中隱約又有一星微光復明而未明,這時一吻既終,男人卻又將手收了回來。
“日後保重。”
蘇紫怔了怔,去咀嚼這四個字的含義;又咳了兩聲,低頭去看手心的玉佩。
原來送的是陪葬之禮。
這實在是一塊美玉,蘇紫竟未捨得推辭,他不回頭,只微朝前躬身行禮,朝外走了十來步,也不再掩飾自己的病態,且行且住,慢慢消失在樹林深處。
章泰正二十五年,莊王薨,公子晗自錢國歸來,同年繼位,改年號“越章”。
章王晗繼位之初,便與各方勢力聯合反攻,一路竟勢如破竹。入夏大破錢軍,立秋錢國覆滅,友邦歃血締約,一致拱章王晗為盟主。章國遷都故錢國境內,後至第三年春,連並三小國,大肆擴張,逼使鄰國稱臣。四載後大局已定,章王立後建儲,便也著手構建一方太平盛世。
驍將李冉虯,自章王晗身為質子時便隨侍左右,戰時屢建奇功,加官進爵,蒙受聖恩浩蕩,竟得與章王同坐並行之恩寵。章王素娛南風,坊間流言一時大盛。然而李冉虯為人耿直,律己甚嚴,且姿色欠奉。蜚語便逐漸沒有了存在的樂趣,
這天秋高氣爽,章王晗忽說要去郊野玩賞秋意,帶了李冉虯出行,所選地點卻是故錢國邊境。
李冉虯忽然也記起了蘇紫,一晃四年,只怕他也已在那荒郊野地,孤單地躺了四年。
故地重遊,身邊卻多了以百計數的禁衛。多年前的顛沛流離似乎只是一場泡影。章王晗有些感慨,四下裡暗自張望,忽見腳前一朵含苞待放的野花,硬生生將正欲踩下的步子挪開。
李冉虯恍然明白他在尋找什麼,環顧左右,地上卻是一片荒蕪;於是傳令禁衛,四處留意,若有發現桔梗,立時高聲通報。
這廂裡軍士散開,章王晗俯身,將那朵野花摘下,放在手心慢慢揉開。卻是尋常的嫩黃色。他歎了口氣,讓花瓣從指尖滑落。
李冉虯忽然記起章王后宮中有著不少豔麗少年,多少都是狡詰圓滑的,也會纏人,然而章王晗卻從未真正寵倖過其中任何一人,就像這落地的黃花。
“阿紫……”這麼多年,他第一次喚起這個名字,“不知睡在何處。”
李冉虯心中一緊,不由安慰道:“王上過慮,蘇紫該是暫居在友人家中,他生性機敏,王上不必為他掛心……”
說到這裡,竟也再編不出說辭,反而想到這話若被蘇紫的亡魂聽見,會不會覺得傷心。
章王晗苦笑道:“孤又如何看不出他有傷在身?當日放他離開,便知道永無再見只可能。”
說著,沉沉地歎了口氣,
聽到這裡,李冉虯再也無力掩飾什麼,便也將蘇紫傷勢的來龍去脈仔細交待了。他看見章王晗手攥成拳,其上青筋著棱,心中想是別有一份煎熬。然面上卻依舊平靜,戴的是朝堂之上的傀面。
章王晗略直了身子,緩緩道:“還記得那青馬的事麼?”
李冉虯略忖,點頭答“是”,便聽章王繼續說道:“青馬之死,罪在過分愚忠。該去時便去,才是最明智之舉。蘇紫隨我這些年,所知甚多,我本應親手除去,然則如此乖巧的人,又怎會不懂其中真意?”
李冉虯聽了他這話,乍時自覺得脊背陣涼,隨即又有些醒悟。
青馬乃是作給蘇紫看的戲文,那蘇紫的故事,此刻又是說給誰聽?
俄而朔風吹過,他突然起了個寒噤,待真正入了隆冬,獵戶的弓箭也該收藏起來了罷。
他正尋思,忽聽遠處的士兵高呼道:
桔梗!
二人忙過去看,但見一片坡地,桔梗尤其旺盛,藍紫色火焰般,卻又文靜的、唯有風吹時露出一絲生氣。
章王晗重賞了兵士,命令閒人退開。兀自佇立在花海之中,似在緬懷,少頃方轉過身來,薄弱地笑道:
“四載春秋,竟就育出了這片花海。而人卻不知哪裡去了,找也找不到……”
李冉虯看他露出了罕見脆弱的表情,心中卻沒有分毫的同情,反而暗暗驚怖。再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言語,於是聽章王繼續喃喃道:
“其實午夜夢回,也曾有心痛難抑。然而等那時間湮沒了,卻也不覺得什麼。我對蘇紫之愛,不過短暫一生,敵不過家國千秋,河山萬里。再想那蘇紫在黃泉之下,一盞湯過奈何橋,也未必會再掛念我這個薄情寡義的人。倒不如這桔梗,年年複生,年年不盡,也用不著為它期期艾艾。”
說到這裡便俯身,要去摘一捧帶走,卻突然“啊”地一聲,痛苦地蹲了下去。
李冉虯以為他身體有恙,忙過來扶,亟待看清了章王手邊的東西,卻也失聲叫了出來。
那被拔起的桔梗根須中纏著一塊翠玉,竟連著白骨森森的一隻手。想是臨死前握住了那塊碧玉,到死也不願放開。
——終——








![<BL>[古代] 《小受世家》BY 逸若辰(小白文,短篇,搞笑)](/ups/27796/post/120x120/578efa4b5afea874.jpg)
![<BL>[現代] 《貓咖小老闆和他男朋友的故事》BY淺海_深藍(完結+番外 短篇)](/ups/27796/post/120x120/578ef53b350975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