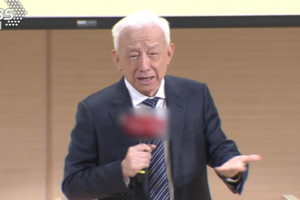這個世界時時刻刻都在萌發新生,滋生罪惡。正值梅雨季節,一個老太太牽著小孫子進了本地最大的超商。他們徑直上到7層,因為今天要去買新出的變形金剛。小孫子卻尿急,嚷著要去廁所。4歲的小男孩已經有了羞恥心,他拒絕跟著奶奶到女廁所尿尿。
奶奶只得送他到對過兒的男廁,然後在門口等著。一字一句地囑咐著:「小心些,慢些。」在門口等了許久,始終見不到小孫子出來。她有些著急,揚聲喊小孫子的名字。
「林林,林林。」沒有回應,也沒有哭聲。
老太太衝進了男廁,幾個正在方便的小年輕都變了臉色,差點尿在褲子上。那天,老太太豁出了自己的老臉,翻遍了男廁每一個隔間。最後,兩眼發黑,昏厥了過去。即使有關部門和相關人士反覆強調,孩子失蹤不用等24小時就能立案。但是每年能破獲的的案件也屈指可數。因為人販子不用24小時,兩分鐘,他就能混進熙攘的人群裡,不著痕跡。
動用一下我們的聰明才智,人販子是怎麼把孩子從奶奶的眼皮底下帶出去的?一條浸有乙醚的毛巾,和一件外套。沒有人會懷疑和小孩前後腳進來的男士,也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貼心的給孩子蓋著衣服防止著涼的父親。他把孩子迷暈,然後扮演了父親的角色。
孩子的媽媽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婆婆,因為她無法面對著一個弄丟自己兒子的人,依舊保持理智。他們報了警,錄了口供,然後事情就一直沒有什麼進展。孩子的家人從最開始的崩潰,到悲傷,然後平靜了。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能夠舍業拋家,用自己的一輩子來找不知道在哪裡的孩子。尋找就像參加了一個興趣班,上到一定的課時就喪失信心了。不同的是,那份悲傷和渴望會如影隨形,讓人夜夜不能成眠。阿七出生在那件事情發生後的第四年。從表面來看,一家三口很圓滿,但是總有些小小的裂縫在加速這個家庭的土崩瓦解。
阿七的媽媽對阿七一直很寬容。哪怕她在家裡上躥下跳,把家裡搞得一團糟,拿畫筆把牆塗成大花臉,剪碎媽媽的裙子給娃娃做衣服。這些都可以被允許。除了出門,說句實話,阿七在小孩子最天真爛漫的日子裡,出去玩的時間屈指可數。她沒有去過大型商場或者超市一次。
小一點的時候,阿七會被媽媽帶著去上班,後來長大了一些,就會被反鎖在家裡。住在高檔社區的好處就是安全,壞處則是阿七就像籠子裡的鳥,沒有鑰匙,哪都去不了。就阿七的問題,她的爸媽討論過很多次,每次都以吵架告終。爸爸摔門而出,媽媽則抱著她一言不發地流眼淚。
「爸爸,我過生日的時候能不能帶我去遊樂場,我的朋友都去過了。」看著阿七可憐兮兮的神情,她的父親用力點了點頭。生日那天,阿七媽媽要出差三天,阿七爸爸則請了三天假。那三天,阿七就像擺脫了韁繩的小馬,撒了歡地玩。
遊樂場、海洋館、樓下的小觀園,最後還在超市抱了滿滿的一堆吃的回家。如果媽媽沒有提前回來的話,阿七會把這次慶祝列為最開心的生日。第三天,阿七的父母爆發了平生以來最大的一次爭吵。「你瘋了嗎!你居然帶她去那麼多危險的地方!」
「阿七是個孩子,她喜歡,也需要去接觸人群。」「你他媽怎麼想的!」「阿七不是小林。老婆,阿七不會丟的。」「姓時的,要不是你媽,小林今年九歲了!」父親像被踩到痛處一樣無力,他垂下了腦袋,悶聲從嗓子裡擠出一句話,「我們離婚吧。」
阿七正目睹著這場家庭悲劇的發生,零食玩具在她腳邊七零八落。 在她看來,自己才是這場家庭悲劇的元凶。她默默地流眼淚,繼而號啕大哭。「我不要你們離婚,不要!我會乖的,不出門,我不出門了!」父親憐惜地抱起阿七,「我的小公主,這些和你沒關係。」
阿七的媽媽對阿七一直很寬容。哪怕她在家裡上躥下跳,把家裡搞得一團糟,拿畫筆把牆塗成大花臉,剪碎媽媽的裙子給娃娃做衣服。這些都可以被允許。除了出門,說句實話,阿七在小孩子最天真爛漫的日子裡,出去玩的時間屈指可數。她沒有去過大型商場或者超市一次。
小一點的時候,阿七會被媽媽帶著去上班,後來長大了一些,就會被反鎖在家裡。住在高檔社區的好處就是安全,壞處則是阿七就像籠子裡的鳥,沒有鑰匙,哪都去不了。就阿七的問題,她的爸媽討論過很多次,每次都以吵架告終。爸爸摔門而出,媽媽則抱著她一言不發地流眼淚。
「爸爸,我過生日的時候能不能帶我去遊樂場,我的朋友都去過了。」看著阿七可憐兮兮的神情,她的父親用力點了點頭。生日那天,阿七媽媽要出差三天,阿七爸爸則請了三天假。那三天,阿七就像擺脫了韁繩的小馬,撒了歡地玩。
遊樂場、海洋館、樓下的小觀園,最後還在超市抱了滿滿的一堆吃的回家。如果媽媽沒有提前回來的話,阿七會把這次慶祝列為最開心的生日。第三天,阿七的父母爆發了平生以來最大的一次爭吵。「你瘋了嗎!你居然帶她去那麼多危險的地方!」
「阿七是個孩子,她喜歡,也需要去接觸人群。」「你他媽怎麼想的!」「阿七不是小林。老婆,阿七不會丟的。」「姓時的,要不是你媽,小林今年九歲了!」父親像被踩到痛處一樣無力,他垂下了腦袋,悶聲從嗓子裡擠出一句話,「我們離婚吧。」
阿七正目睹著這場家庭悲劇的發生,零食玩具在她腳邊七零八落。 在她看來,自己才是這場家庭悲劇的元凶。她默默地流眼淚,繼而號啕大哭。「我不要你們離婚,不要!我會乖的,不出門,我不出門了!」父親憐惜地抱起阿七,「我的小公主,這些和你沒關係。」
然後他親了親阿七的額頭,給她擦眼淚,低聲地安撫她。不得不說,他是個好父親,溫柔又真誠。阿七的母親冷眼看著眼前的這一幕,突然間掩面失聲痛哭。東西被歸置回原位,一場鬧劇落下了帷幕。在相隔了幾百公裡的一個村莊,那家人很貧窮,過著數著米粒下鍋的日子。吃著雞腿的小皇帝,落魄成了乞丐。
最開始的時候,時林總哭。在想到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的時候哭。還有被那個莊稼漢抱起來,很親暱地親時林的臉蛋,喊他兒子的時候哭。時林的臉蛋總被那些硬硬的胡碴紮得生疼。家裡的女主人會笑話時林嬌氣,然後嗔怪地推一把丈夫。反正在外人看著,這個花錢買來的家也很幸福。老婆是買的,兒子是買的,這個貧窮的男人不在意。
不過他總對外講,這個兒子是寄養在親戚家的,剛剛接回來。村民都知道這個孩子是買來的,因為五叔趁著夜色進了他的家門。五叔是這片人販子網路的小組長,負責聯繫買家、賣家。用他的話說,賺點辛苦錢。他的確挺辛苦的,費盡心思地把自己往不歸路上送。因為這對夫妻準備的錢不夠,剛出生的嬰兒一轉手成了別人的兒子。他們的錢只夠買時林的。斟酌再三,他們花錢買下了時林。時林挺好看的,有長睫毛和酒窩,一看就是城裡的小孩。
給嬰兒準備的衣服時林穿不了,自己的衣服又被五叔扒走了。在這個陌生的地方過的第一夜,時林的睡衣是一件破洞的,快看不出顏色的大背心。他甚至連條小內褲都沒有,他最愛的小鴨子內褲因為尿濕了,被丟在爐子旁邊。時林被餵了一次安眠藥,醒來的時候,他不得不面對人生最重大的變故。這裡沒有變形金剛,只有廉價的草蛐蛐。
這裡沒有光潔的馬桶,一個坑,兩塊板,夏天蒼蠅和臭蟲在這兒分娩。時林甚至有一次見到了一隻小刺蝟。這裡沒有睡衣,時林整個夏天都光著膀子跑來跑去。時林最開始哇哇地哭個不停,他要找爸爸媽媽,都被那個男人板著臉瞪回去。「你媽不要你了,以後我們就是你爸媽!」我們不知道這個小孩子內心經歷了多大的痛苦。在日復一日的洗腦下,時林不再反抗,甚至開口叫他們爸媽。時林這個名字是他身上唯一和過去有關的標記,也在後來成功地被剝奪了。
他們叫他,小軍。我們不知道他們給這個四歲的小孩洗腦用了多久的時間,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時林穿不慣滌綸面料的衣服。他因為那件衣服起了一身紅疹,被男人抱著送到了村裡的診所。時林到現在都能懷念起那個溫暖的肩頭,那種關懷是他親生父親很少對他流露的情緒。這個厚實的莊稼漢讓小小的時林有了依靠的感覺。村醫有很濃重的口音。他給時林開了一管藥膏,叮囑了很多事情,特別是要給時林穿純棉布的衣服。
莊稼漢掏錢在集市上一口氣買了好幾件純棉的衣服,很貴。但是他非常驕傲地說:「我兒子金貴著呢。」時林開始逐漸適應了在那裡的日子,他在那裡是大將軍,泥土和大山都聽他號令。將近年末的時候,一家愁雲慘淡,一家喜氣洋洋。時林的養母懷孕了,最開始孕吐被當作吃壞了東西。女人都有天生的直覺吧,她能預感到自己的子宮裡正有一個小生命在生長。莊稼漢迎來了自己的親生孩子,一同來的還有更加赤貧的生活。他沒有足夠的錢去養育兩個孩子,他們討論過把時林送出去。
但是懷孕的母親更能感同身受,她擔心那家人會對時林不夠好,不給他穿棉布的衣服。
時林終究是留下了,過著期盼小孩子出生陪他一起玩的日子。孩子在一個秋季出生了,五歲的時林那時正在拔田埂上的枯草。是個小男孩,出乎意料的壯實。與此同時,時林的親生父母也準備用一個新生命來代替自己的失子之痛。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來平復失去時林的痛苦,用了一年的時間孕育。第三年,阿七出生了。時林這個時候七歲了,他的親生妹妹剛剛過了一周歲的生日。如果兩個人面對面站著,眉眼之間能看出相似的感覺,也很容易就能分出階級門第。
時林在那裡過得很開心,即使他營養不良,會被很多小孩子欺負。但那個壯得像頭小牛犢似的弟弟會把所有欺負他的人都教訓一遍。
相差4歲的兄弟,弟弟反而更像哥哥。不管是體格還是勇氣。他們一家很窮,唯一的一本兒童讀物是在路邊撿到的《喜羊羊與灰太狼》。但是時林一年四季始終都穿棉布的衣服,一次無意和弟弟穿混了衣服,時林的一身紅疹把弟弟嚇壞了。從那以後,他嚴格區分自己和時林的衣服,像個雄赳赳的小衛士,防止出一點差錯。
我們可能會放棄尋找,但是那不代表有了線索的時候我們不會欣喜若狂。阿七7歲那年,五叔被抓了。員警順藤摸瓜找出了一堆失蹤兒童的下落。那對貧窮的夫婦完成了一件誰都沒有想到的「天才之作」。狸貓換太子,把自己的兒子「還給」時林的父母。所有的資訊,甚至於一件棉布的衣服。天衣無縫。那天他們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推出去,懦弱惶恐的樣子被展現得淋漓盡致。時林14歲,弟弟10歲。但是他們兩個看起來的年紀卻像調了個個兒。這樣的對比之下,時林的媽媽不會懷疑什麼。也沒人會在那種情況下懷疑什麼。
失而復得的喜悅和激動足夠沖刷掉全部的疑點。時林一直縮在角落裡,當初無法無天的小老虎也變得懂事了。
「你們還是不是人!你們自己有孩子為什麼還要搶我的小林!」時林的媽媽一直很激動地罵,用了她所知的全部髒話。
時林的爸爸默默地抱緊妻子,這個男人眼角濕潤著。為了不讓事態變得棘手,他忍住了跳起來暴打眼前這對夫妻的火氣。陪同來的民警看著眼前的場景,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有個女警在偷偷地抹眼淚。弟弟被抱在時林的親媽懷裡,時林站在距離母親幾步的位置。
他一步一步走到自己的親生母親眼前,義正言辭地說:「不許罵我爸媽!」我們有理由相信,時林的親生母親在那一刻有懷疑過眼前的這個男孩,是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時林的眉眼間有藏不住的血親間特有的相似之處,但是她相信不會有親生父母願意把孩子送給一對陌生人。「你得給我爸媽一萬塊錢(約5萬台幣),養大他不容易。」是了,自己的兒子才不會做出向別人伸手要錢的舉動。
養父母的心一直懸著,如果被看破了,功虧一簣,或許會被抓去坐牢。他們很緊張,一把把時林抓到身後,呵斥道:「小軍,別鬧了!」時林很委屈,他只是想為這個家做些什麼而已。
村醫說,母親的病很嚴重,得儘快治療。這個貧窮的家庭已經舉步維艱,帶走了弟弟,也就相當於帶走了這個家裡的一個勞動力。在我們的認知裡,10歲的小孩能做什麼?看電視、玩玩具、遊戲,或者是沒完沒了的作業。偶爾幫忙打一盆洗腳水就算是懂事了。
你可以試著把這個問題拿去詢問自己的父輩,得到的答案可能會是天差地別的待遇。打豬草、洗衣做飯、在泥土裡摸爬滾打,虎虎生風。我們必須要承認,大多數貧窮的少年會和土地為伍一輩子。
他們還在過著70年代或者更加久遠的生活,沒吃過比麵條更好的東西。總之,弟弟被帶走了。養父母鬆了一口氣,但是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裡,他們終日要良心不安。沒人知道他們是怎樣說服一個孩子離開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們可見的事實就是,那個孩子從頭到尾眼睛裡面都蓄滿了淚水,就像暴雨過後的池塘。當時林在那塊小小的土地裡刨食的時候,他的親妹妹阿七不得不耗費一些時間去接受自己莫名其妙多出來的哥哥。那對父母把自己的兒子教育得還不錯,有基本的禮貌,也不恃強淩弱。雖然他非法佔有了時林的身份,和家庭。
阿七叫他,小哥哥。他叫阿七,小妹妹。兄親妹恭,和諧又親暱。很多親戚來看他們家裡失而復得的小寶貝,每個人都很激動地擁抱他,這其中還有時林的奶奶。
整整十年的時間,丟失孫子的痛苦讓這個老太太迅速蒼老下去。這是她十年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孫子」,也是七年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孫女。這些年來,阿七的一切都和她這個奶奶無關。時間緘默地劃清了她和兒媳一切的界限。
逢年過節,一直是兒子一個人回來,天倫之樂從十年前的那個意外開始,已經不復存在了。她從來沒有怪過兒媳的刻薄,在她看來,她和時林媽媽的角色不僅僅是婆婆和兒媳。更是母親和女兒。
身為一個母親,她完全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一個母親的崩潰與悲傷。就像此刻,兩個母親,抱在一起放聲痛哭。那個男孩開始經歷時林所經歷的一切。新的父母,新的環境,和每天晚上哭紅的眼圈。他被送去上學,上戶口,擁有一個新的身份。他不用再背朝黃土,撅著屁股幹活,他有了新的朋友、家人。他活得很幸福,即使他不得不遇到一些窘迫的事情。比如他不會用熱水器,一下子被燙紅了皮膚。他不會打遊戲和用網路用語罵人,在一群城市小孩子裡他顯得像個怪胎。
但是他很聰明,腦袋裡裝滿了鄉野。比如怎麼逮蛐蛐、螞蚱,怎麼學老牛哞哞叫,怎麼編個草兔子。這些,都對生活在童話故事裡的孩子有致命的吸引力。他很快交到了同齡的朋友,學著說正宗的普通話。他對阿七很好,他總覺得自己有義務照顧好這個小妹妹。他給阿七講故事,陪她玩過家家,幫她洗弄髒的衣服,因為阿七怕被媽媽責備。
阿七逐漸習慣了有什麼事情都去找哥哥解決,或許在她心裡,哥哥比焦慮的媽媽還有忙碌的爸爸更加靠譜。「哥哥,有人欺負我。」兩個孩子念同一所學校,男孩就像保護時林一樣保護他的小妹妹。他找到那個欺負妹妹的男生,並且一拳打出鼻血。同學在那裡吶喊助威,一直到老師來把他們分開。老師叫了家長,並且各打五十大板地批評了一頓。男孩出了辦公室的門,一眼就看到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阿七。他走過去,輕輕摸了摸阿七的腦袋,小聲地說:「沒事,我沒有把你供出去哦。」
阿七哭得更大聲了,父母看著眼前的一雙兒女,批評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阿七越來越習慣生活裡出現一個哥哥,反倒是她的媽媽開始越來越焦慮。她甚至總待在家裡看著兩兄妹,不讓他們上學。只因為她會感覺自己心很慌。誰都說不好媽媽的特異功能,但是當她的丈夫和她交談了幾次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個女人瘋了。她的護子心切已經發展到了病態的地步。有一次,她剛剛答應了男孩到他的朋友家住一晚。可不出三個小時,她就神經質地命令丈夫去把男孩接回家。男孩在晚飯前回到了家,只是身上的衣服不是出門的那一件。在時林媽媽的詢問下,我們得知了整件事情的經過。男孩和朋友在浴室裡打水仗,弄濕了衣服。所以男孩穿著朋友的衣服回了家。當天晚上,時林的媽媽預備把衣服洗乾淨。第二天由自己的兒子把衣服還回去,並且致謝。
然後,她就看到了這樣的字眼。滌綸20%,棉80%。可疑的是,男孩身上並沒有出現紅疹。
弄巧成拙的是這樣的一句話,「他穿『滌綸』的衣裳過敏。」時林媽媽還記得自己鄙夷地回了一句話,「我自己的兒子,我自己清楚。」應該說,時林的媽媽從第一面就心有疑慮,但是她不想也無法再承受一次失去和尋找的痛苦。即使這個男孩剛剛融入這個家庭不到一年的時間,他聰明、真誠、討人歡心。那天,時林的媽媽拿著先前的DNA檢測報告看了許久。她沒有辦法找時林的父親商量,因為他們已經分居很久了。在找回兒子後,那個男人反而不能忍受她的一切。他說自己受夠了,他和在酒吧認識的女人雙宿雙棲,每天晚上在孩子睡著以後溜出家門。他們達成了協議,等阿七18歲後就去離婚。她只能把DNA報告鎖回保險箱,然後壓下疑慮,風平浪靜地生活。她已經沒有心力去拆穿任何陰謀或者詭計,她只想守著自己的孩子好好生活而已。時間總是轉瞬即逝,沙漏是計量時間最好的辦法,因為我們可以一點一滴地看著時間流走。
同樣,我們也能從孩子的身上看到時間的強大。阿七和男孩越長越大,他們有相仿的氣質,卻沒有相似的眉眼。不過還是像小時候那樣形影不離,阿七說:「我想談戀愛。」男孩語重心長地教育她,「莫讓臭小子騙了。」兄妹倆笑成一團,沒有時間去在意父母間岌岌可危的婚姻。不過,七年的時間足夠發生很多事情。沒等到阿七18歲,時林的父母就離婚了。阿七那天哭得很傷心,但是依舊阻止不了父母的婚姻被一撕兩半。「你們想跟誰?」「你們能不能不離婚?」「你是大人了,小七。」母親這樣說,面無表情,她用了很久的時間來消化這個事實,但是她卻不想給孩子一點解釋。
阿七崩潰地大哭,就像之前一樣。父親說:「這和你們沒關係。」「你們不要我們了!」男孩手足無措地站著,妹妹的哭泣讓他很難受。他過去,像個男人一樣抱住妹妹說:「沒事,我要你。」他和妹妹拉勾勾,並且承諾不管怎麼樣都不會離開她。這場離婚速戰速決,父親很快搬了出去,也帶他們見了他的新女友。父母離婚的悲傷剛消退,新的悲傷就捲土重來。時林的養母因為肝癌過世了。
那是男孩八年之後,重新回到那個鄉下的家。他已經是個城裡人了,和這個村子格格不入。他帶著眼淚離開,又帶著眼淚回來。日復一日的勞作也讓時林的體格和自己的兄弟迅速拉近了距離。他不再白白凈凈的,也不再瘦弱,他已經學會怎麼樣去承擔一個家庭的責任。只是長相越來越像自己的父親。所以阿七見他第一面的時候,就驚呼,他和爸爸長得很像。親兄妹倆沒在出生時見到,卻在養母的葬禮上遇到。那一刻,真相正在蠢蠢欲動,它在等待著天下大白的那一分鐘。
村間的葬禮在吃過飯以後就散了,那個小小的家沒有什麼新的改變。只是牆上多了一張全家福。男孩在葬禮上流淚,看著時林忙前忙後地處理事情,自己好像個客人。他很想握著自己父親的手說點什麼,卻發現什麼話都顯得疏遠客套。時林的養父把他們讓進去坐下,他的年紀其實和時林的親生父親相差無幾,但是喪妻之痛和臉上的皺紋讓他看起來很老。他看著自己的親生兒子,向時林的母親開口,
「大妹子,我對不起你哇。我騙了你們這麼多年,遭報應了啊,遭報應了。」
我們怎麼確定被拐人口的身份呢?驗血、DNA。那麼怎麼讓用來確認身份的DNA出錯呢?很簡單,調換標籤。在員警和醫生要來抽血化驗的前一個晚上,村長敲開了他們家的門。言簡意賅來說,來的那個員警是村長的侄子,他可以幫忙調換兩個孩子的血樣標籤。條件是,一萬元,和一張選票。員警需要一萬元娶親,村長需要下次選舉的一張選票。而這對貧窮的夫妻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金鳳凰。這個交易聽起來很公平,除了對時林而言。人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違心或者違法。那一萬元是東拼西湊借來給時林養母的救命錢,但是她卻想換給自己的孩子一個錦繡的未來。
起床去小解的時林聽到了這場針對他的陰謀,但是他選擇體諒。他擁有一顆聖人的心,和自私的心思。
在他的潛意識裡自己因為養父母被迫離開家,而且他也受夠了適應新環境的痛苦和無助。所以讓弟弟去嘗嘗這個苦頭,就當作報復吧。
養父和盤托出後的內疚、時林親生母親的眼淚、弟弟的不安和羞愧、親妹妹拚命攥住弟弟的手掌……這些在22歲的時林的眼睛裡成了一幅會流動的畫。他點燃了一根煙捲,吧嗒吧嗒地抽,然後伸出滿是老繭的手,沖著自己親生母親說。「阿姨,你好,我叫小軍。」時林非常清楚自己說這句話意味著什麼, 時林跟著養父親繼續在一畝三分田上勞作。男孩和妹妹跟著父母回城裡,繼續用功讀書。
什麼都定格了,再也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