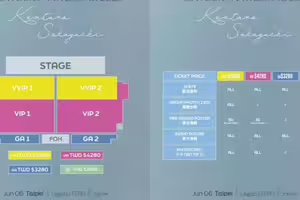在我透露了有意創業的消息後,有的朋友建議我「不妨找台灣籍員工」。我和關先生討論過,覺得時機尚早。想要先在日本站穩腳跟,不採用全套日式待客方式,無法勝任。這起頭的一步,非日本員工不行。
什麼叫做「日式的待客方式」?常去日本觀光的人,必然對於日本服務業笑臉迎人的待客之道,印象深刻。儘管近年來,關於日本服務品質大不如前的指摘,時有所聞,但放眼全世界,能做到像日本服務業這般以客為尊的,仍舊不多。這一點,光是在機場國門就能感受得到。某些國家的機場巴士售票窗口,乘客上前詢問時,只見鏖戰手機遊戲的售票員,意興闌珊地將手機置到一旁,勉強應客;或者禮品店服務員談興正濃,心不在焉。凡此景象,只要踏上日本第一天,就覺得跨過楚河漢界一般,氣象一新,似乎全國上下都繃緊了神經,笑臉迎接四方來客。
無怪乎日本以「おもてなし(款待)」作為競爭標語,打敗競爭對手,贏得了2020年夏季奧運的主辦權。世上除了日本,誰敢號稱自己「款待來客」的精神,獨步全球?
但日式服務,真的只有笑臉、熱情,可以道盡一切?
只要試過在日本店家買東西,大概都會注意到一點。商家老闆會因為客人所洽詢的商品碰巧缺貨,臉上浮現「抱歉已極、愛莫能助」的表情,這表情做到極致,近乎哭喪著臉。所以,世人皆知日本商家待客,重在「熱情能笑」,往往忘了日本商家待客,「同情善哭」,也是等量齊觀,一樣重要。
所謂「同情善哭」,與日本人「精於道歉」,互為表裡。哪怕對日語僅有初學程度,您也必然能從商家的口中,聽出那如連珠炮般、飽含歉意的「すみません(對不起)」。這並非全為了表達對客戶「過意不去」,「すみません」發生在收錢、找零,甚至轉身、目送,與歉意不完全聯繫上關係。
「熱情能笑」好學,「同情善哭」就不好模仿了。這多少要放下點自尊,豈是外人輕鬆能學?
有個在台灣工作過的日本人告訴我:他在台灣職場,最無法適應的事,就是台灣人面對他人在工作上的指摘,第一反應是先大呼「怎麼可能」,採取防衛姿勢,再進行對話;日本人則是先說「すみません」,各退一步,再進行對話。
職場如此,台灣一般商店也不習慣道歉。我有過幾次短暫回國期間,向店家洽詢商品,一句「賣完囉」,對話便戛然而止,仁至義盡。對於台灣人而言,「道歉」確實不是我們的強項,尤其錯不在己時,更難把道歉說出口。我若久居台灣,這些都是我耳熟能詳的,根本無需大驚小怪。但如今在日本待久了,偶然回國,聽到同胞近乎打發式的回覆,心中居然有了「受創」之感(套句當今網路常用語:玻璃心碎一地)。所謂「由奢返儉難」,日式服務就是讓人覺得活在備受尊重的奢侈裡,再難回到我本應熟悉的服務態度。
「能一舉網羅優秀的員工,特別是客服人員,我們就是如虎添翼了!」
週六晚,我依約與關先生夫婦在一家烤肉餐廳見面,預計要來的三名挖角對象尚未現身,我等待之餘,透露了我的期許。
關太太笑道:「你放心,我和她們相處得很好,知道她們都是工作認真的人。」
「那就好。」
「只是,跳槽的事情,茲事體大。我已經和她們說,我們會以『正社員』聘請他們。不然,就難以吸引她們跳槽。」
日本企業由於愈來愈倚賴「派遣員工」,無正職的日本人與日俱增。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派遣員工被日本公司大量解聘,有五百多名失業的派遣員工在東京都中心日比谷公園露宿過年,這景象震撼了日本全國。公司剛成立就只想採用「派遣員工」,絕對吸引不到好的人才。
一旦以「正社員」(正職員工)聘請,依據日本勞動相關法律,公司無「客觀合理的理由」或「社會上通用常識」,是無法任意解僱員工。說得極端點,你開了餐廳,請了一群做飯的夥計;後來餐廳不做,改開理髮廳,這些燒飯的夥計縱使不會剃頭,你也得為他們在理髮廳找份工作,掃地擦桌子都行。總之,你也不能貿然請員工走路。除非公司倒閉,或員工自行離職,我們都有義務一直照顧她們的生計。這對我們而言,是個非挑不可的擔子。
關太太說:「今天我除了盡力說服她們,還得靠你的助攻(後押し)。你親自出面,說公司經營可靠、商品供貨沒問題,讓她們安心轉職。」
關先生接著半嚴肅地說:「侯桑,認真點,別像平常那樣愛開玩笑呀!」
說實在,我不太確定自己的臨門一腳,是否真有助益。我就算有如鼓舌簧,畢竟還是得透過日語來表達,這力道就減了一半。
不久,三名員工陸續來到:三木、中井、川田。三位小姐看上去都不超過三十歲。中井、川田專長在於網頁設計,三木則是客服人員。
幾個女孩都能喝,邊喝邊談著公司的大小事,把我晾在一邊,我也正好藉機觀察這三位將來可能共事的員工。
中井、川田笑逐顏開,頗為可愛,但真正談笑風生的,則是三木。關太太說過,三木是「ムードメーカー(帶動氣氛者)」,既適合對外應客,也有助於調和辦公室氣氛。
三人皆能為我所用否?
大家談著現在公司的種種。三木開始模仿起她們老闆的口頭禪,用著滑稽的關西腔(大阪一帶的方言):「アホか、こいつ(蠢貨嗎,這小子)?」
說完,大家大笑。三個女孩子,都是從「短期大學」(短大)畢業。這是種日本特有的教育制度,有一點像我國的專科學校。老一輩日本人的印象裡,「短大」是專門培養好媳婦的所在,銀行的客服窗口最樂意錄用這樣的女孩子,大企業招募客服新人,從「短大」成批物色畢業女生,是最省事的做法。短大的女孩子,進了公司、做起總務、社內戀愛、結婚辭職,人生軌道鋪設得有條不紊。現在男女職場機會力求平等,情形固然起了一點變化,但客人造訪,端茶招呼的,必然是女孩子,不做他想。
台灣人總覺得日本女孩子「有女人味」,那是社會期待如此,日本大企業也將這類旨在相夫教子的日本女孩視為男職員的「福利」:男人進了大企業,只要苦幹實幹,不僅終身收入無虞,連太太都幫著預備好(最終當然仍是各憑本事)。對男女期待不同,這事自然不好明著說,但全都在日本職場空氣中瀰漫得心照不宣。附帶一提:社內戀愛(公司內戀愛)對於日本女孩子而言,還是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想要在社內維持清純形象,總不能交往了中村先生,再交往上村、下村,一村一村地交吧?
可以說,日本女子,尤其是短大畢業的日本女子,其「女人味」是學校、職場一貫作業下培養出來的。如此這般,我既有心於做日本女人的生意,放手讓這些女人中的女人來做,才是唯一的出路。
倒是她們口中揶揄的「老闆」,似乎不怎麼受這些日本女子的待見。從她們言談中,我約略拼湊出這位關西老闆的形象:大阪人,娶了個上海太太、在郵購服飾尚在啟蒙時期,他搶先一步著眼於此,透過上海太太的穿針引線,進口中國廉價的女士禮服,以此暴得大富。
「公司每年營業額好幾億,但是我們進公司以來,三、四年了,薪資沒調整過一毛,分紅也少得可憐。看不出來老闆對於每一個員工有著甚麼長遠規劃。」三木說道。 「使い捨てです(把我們用過就扔)。」川田接著說。
「自分が得することしか考えないです(只追求利己)。」中井也補上一句。
看來對於老闆的反感,是有志一同了。大阪商人聞名於日本商界,當中又以「堺商人」稱霸四個世紀(堺是大阪府中部的都市)。從前堺商人得利於「日明貿易」,也就是與大明王朝的進出口,產生出一群貨殖長才。與這位大阪老闆轉賣中國商品,從中牟利,其生財之路,如出一轍。將本求利,固然是商業經營的鐵則,但日本的流行成衣業似乎走了偏鋒。日本某家大型服飾公司,三令五申「不許加班」,實則店鋪打烊,要到晚上十時至十一時之間,其後清點庫存、整理賣場、準備翌日商品,總要弄到凌晨。這些非加班不可的活兒,全在帳上消失無蹤,員工只有盡心盡力配合公司「無加班」政策,多做無賞,少做有罰。這家公司長年如此,屢屢成為媒體關注的「黑心企業」,近幾年為了洗刷企業面貌,將一萬多名非正職員工登用為「正社員」,享受正職待遇,卻始終擺脫不了舊日黑心形象,形象問題拖累公司,陷入業績不振的惡性循環。
看來關太太沒說錯,這幾名員工都有異動的想法。只是,有心異動是一回事,願不願意加入我們新成立的公司,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對關太太使了個眼色。關太太意會,隨即做了個起頭。
「大家難得聚在一起,我就開門見山談談我們的計畫。」關太太道。
關太太道:「侯桑在此,也想知道大家的意思。大家都聽說了,我和我先生有意開一家服飾網購公司,侯桑是我們的合夥人。為此,我也向公司提出辭呈。可以說,我是一往無前了。」
眾人點了點頭。關太太繼續說:「我是無所謂,反正我有先生養我。我做不好,最多回頭做家庭主婦。各位既然都有離職的意願,我們就……?」
三名女孩子未發言,偶爾只聽到三木傳來「嗯」的應和聲,不知可否。
「我必須把話說在前頭:這開頭會是一家小公司,但有了妳們,我相信公司必能成長。」關太太說著,把眼光朝向我,希望我發言。
我看看差不多了,喝了口水後,放下水杯,開口道:「首先,謝謝各位今晚賞光,大家不拘形式,就當是認識朋友。畢竟,大家平時聚餐吃飯,連活魚都吃過,沒看到過從台灣進口個活人吧?」
語畢,女孩子們先是愣了半晌,隨即爆笑如雷。關太太也忍俊不禁,笑了出來。我表情不變,清了清喉嚨,繼續道:
「開一家新公司,有風險;加入一家新公司,同樣有風險。各位知道阻撓我們前進的,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困難、障礙,而是那些看都沒看到的風險。人們只要想到有風險,就裹足不前,最後就是一事無成。」
「很多人,一生避開了所有的風險,在無災無難中度過。這是他的人生態度,百年之後,他墓碑上面就留個名字,其他甚麼也不是;墓碑再要風化,他就連名字都留不下來(墓石は風化してしまったら、名前も殘らない)。」
「但是敢於承擔風險的人,不一樣。機會是留給這樣的人。不朽的墓碑也是留給這樣的人。我身為一個外國人,卻在日本走上創業這條路,所承擔的風險比我自己的家鄉來得高。但我敢於這麼做,關先生與關太太也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們眼中看到的是希望,讓我們願意接受所有挑戰。」
「我投資最多,扛起了最大責任,我也說服了中國的供應商,新商品三個月後就會到。我相信日後商品也不成問題,僅管我『風險』不離口,但絕非盲目,事實上是萬事俱備。我唯一欠缺的,就是像各位這樣有能力的員工。請各位加入我們!只要妳們幫著我們走這開頭的幾里路,日後公司成長壯大,就是公司回饋妳們,讓妳們決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幾個女孩鴉雀無聲地聽完了我的說話。這番精心設計的演說,日語大致無誤,我見到女孩子們邊聽邊點頭,全都懂得我要說的意思。只是,這到底造成了多大效果,我毫無把握。
「あの(嗯)……」三木小姐開口說話了:「侯桑,不知您為何說得這麼認真。我們早就答應了,要到貴公司效勞呀。」
中井也說:「您不用擔心,我們加入了!」
早答應加入了?我為了今晚的「演說」,輾轉反側好些日子,早知這幾個女孩要加入,我犯得著這樣動情地講演?
眾人再度舉起酒杯,齊聲為公司的未來「乾杯」,我為了剛剛的演說用情過深,半天回不過神,胡亂地喝了幾口,隨即到廁所尿遁,免得尷尬。關先生也跟著進廁所。兩人面對著牆小解。
「什麼時候知道的?」我問道。
「什麼『什麼時候』?」關先生反問。
我敲了一下他的頭:「這幾個女孩早答應加入我們公司,你怎麼不告訴我?害我在那裡情真意切地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