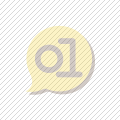我最近突然想起林。對她我不知道要從何說起,但是那段和她在一起不長的日子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想起我開始對她的驚訝,後來的同情,再後來的厭惡,直到產生恐懼感而不得不搬離了那棟房子。突然很想把住在林家發生的故事寫出來,不知為什麼一直想和她聯繫,想要知道她怎麼樣了。但是卻一直猶豫要以什麼方式?朋友?房客?還是……
那是留學加拿大的時候。1997年的冬天,我所居住的學生宿舍下因為要建地鐵,所以大學把我們的宿舍賣給了多倫多市政管理機構。我們這些住在裡面的學生只好搬離。聽說今年冬天多倫多會特別寒冷,雖然找房子應該不是問題,但是再也不可能找到像我們宿舍這樣便宜的住處了,身在異鄉心裡覺得特別的蕭條,淒涼。每天都在不停的看報紙找地方。
後來我終於在一張中文報上看到一條消息,是間地下室,有自己的衛生間。每月竟然比宿舍還便宜。急忙打了電話,對方是一個聲音有些啞啞的低沉的女聲,聽口音像中國北方人。我趕緊套了半天近乎,覺得很親切。她冷冷地應了幾句,就叫我趕緊去看房子。
房子在市中心,靠近唐人街,是個極老的住宅區。整條街看上去都飄著沉土,霧濛濛的。我覺得心情很壓抑,也不知道為什麼。房東是個高大的北方女人,皮膚很白,但是透著股灰暗。她說她叫林,上來就說要預先付兩個月的房租,而且如果住不到半年,預付的就不退還。然後她叼著煙捲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那眼神讓我覺得像是老鴇在挑女孩子,心裡說不出的厭惡。她看了我半天,咧了咧嘴,從叼著煙的嘴裡擠出一聲輕笑。
“看你的樣子,什麼都沒見過吧?”我沒聽懂她的話,愣了一陣。“我怕你住不慣我很吵的。”她掐滅了煙,微眯著化得煙熏般的雙眼瞟著我。
“應該沒問題。我能不能先看房子。”我覺得奇怪,租房子給人還要醜話說前頭,再說能吵成什麼樣。我在迪廳都能睡。地下室比樓上顯得乾淨,只是有些塵土,至少沒有樓上那種滿是奇怪味道的空氣。而且一邊還是通往後院的門,採光也不錯。這是一棟建在坡上的房子,後院是向下傾斜的。所以房子的地下室嚴格說起來只是鄰街的那一邊,而院子的這一邊就是一層。房子的一層在院子這邊是二層。而且有個搭建的木制涼臺伸出來,這樣結構的地下室只這麼點錢太划算了。看著我渴望的眼神,她冷笑了一下。
“行,你這兩天搬吧。不過合同簽了可別後悔。”
我當時是不明白有什麼好後悔的,但是怎麼也不會沒想到從那天就開始了一段噩夢……
搬進去第一天晚上,一陣如戰場上殺敵般的噪音把我從夢中吵醒。我看到房頂的吊燈在搖晃,聽到樓上東西砸落的聲音,以為地震。清醒後聽到女房東殺豬般的尖叫聲,是搶劫!我抄起身邊的網球拍就向院子沖了出去,等我從下面涼臺的木制縫隙看上去,驚呆了。隱約見到幾條腿以奇怪的方式羅列著。其中還有兩條是黑赫色的。我大概看到一個黑人,一個白人,還有林。她仍舊尖叫著。像一場戰鬥,他們三個在木檯子上奮戰著。震得木屑全部抖落在呆若木雞的我身上,我愣了半天,明白這不是搶劫,是林的生活。我無權干涉,而且我簽了合同,半年時間還能天天如此?我回屋睡了。
早上,她在廚房裡抽煙。“昨晚睡得好嗎?”嘲笑一樣地看著我。
我沒說什麼,她起身經過我身邊,突然伸手在我臀部掐了一下,我驚叫。
“不錯,挺緊。”笑著離去。我以前也經常摸女同學的臀部,是開玩笑,但是她的舉動讓我覺得很奇異,說不上是討厭還是驚訝。
我入住的第二天,下午放學從超市買了各種打掃廚房的清潔液。我不能在那樣一個佈滿油泥的廚房裡做飯吃,不習慣。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儘管林沒有帶男人來。我反復的想如果毀約我的損失將是多少,還是要忍受下去。最後決定還是先去洗廚房,特別是那個水槽。我一邊用強力的消毒液拼命地擦拭著那個水槽一邊想,我還能用在這裡洗幾天碗,幾天菜。
“你以為這樣就能抵消你白天的免費觀賞?”林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門口。“什麼?”我沒聽明白。
看到我驚鄂的表情她突然大笑起來,“說你什麼都沒見過吧!真土。”她走過來在餐桌旁坐下。“喂!別擦了,你是房客,又不是我顧的女傭。”
“沒事。”我知道我是為了我自己擦而不是為她,自從搬進來連洗手的次數都是以前的兩倍。
我陪她去打胎
“跟你商量個事,你明天有空嗎?陪我去趟診所。”
“你病了?”聽我這樣問,她突然笑得前仰後合。“你這小姑娘,真有意思,好了記得明天陪我去,我去睡了。”說著離去了。
那間診所是我見過的最髒的醫院。在唐人街一棟很舊的大樓的四樓。門口沒什麼標誌,看上去是間普通的公寓。進去就能看到有護士負責掛號,等著的病人塞滿了一屋子,門戶緊閉著,充斥著一股很噁心的腐爛味道。
林就在這家非法診所裡打胎,她說她來過幾次,還挺不錯的。我看著牆面上一塊一塊像是噴濺上去的暗棕色污點,不禁打了個冷戰。我不知坐了多久,林從裡屋走了出來,臉色蒼白了許多。走路也有些不穩,額頭上還有汗珠。她緊抓著我的肩膀,靠在我身上。
“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