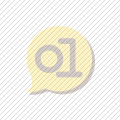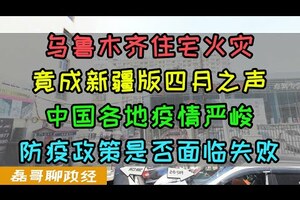真正的溫柔,是給悲傷的人一個擁抱
文/凌性傑
父親的葬禮
父親去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個快樂的孩子。身為長孫,我領取了家族成員各種理所當然的愛。如果沒有意外,我的父親可能會像我舅舅那樣,累積足夠資本之後自行創業,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裡成為一個小老闆。我在成長歷程裡,將會崇拜他的意氣風發,也會看見他在機具之間揮汗工作的身影。他會用勞動所得帶著妻兒四處旅行,讓心愛的孩子盡情享受蘋果的滋味,栽培下一代受最好的教育。在小姑姑眼中,這個長兄是最聰明最能讀書的,只可惜家境不允許他繼續升學。但那又何妨,他還是靠著自己的努力創造了幸福。
就在那樣美好的日子裡,我們擁有整潔明亮的庭院,以及無憂慮的日常。本來無事的春日午後,父親職場意外消息傳來,讓這個家幾乎喪失對幸福的想像。
父親過世,留下不到三十歲的媽媽和三個孩子
去認屍之前,我偷偷聽見祖母交代母親,如果孩子到了那邊沒有哭,就用力擰他們,讓他們哭。那一定是父親想多賺點加班費,於是趁著午休吃飯時間自願去清理砂石儲存槽的機械。那樣的工作,本來應該有人在一旁看守並且管制現場的。不知道為什麼,看守的人暫離職守,砂石車司機也沒檢視現場,就直接把砂石倒進儲存槽。
後來呢,我爸就沒有後來了。在我第一次見證死亡的現場──躺在地上的父親滿身塵埃,媽媽嘶啞地哭泣,她不到三十歲,旁邊的孩子分別是七歲、五歲、三歲。三個小孩沒有被擰,媽媽哭我們也就跟著哭了。
沒有人可以怪罪,是多麼痛苦的事
讀書時曾有人不識相地問,你爸是怎麼死的?我一律冷冷回應,工作意外,請對方閉嘴,其他再不願多談。這或許是我意識到尊重他人隱私的起點。別人不想說出口的事,我就不去問。相對地,我也不喜歡被窺探被干擾。
至今我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當時肇禍的人到底是誰。只知道有人奪去了我的幸福,而那些人賠錢了事之後就消失了。我沒人可以怪罪,就只能怪命運了。電影《橫山家之味》裡,承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如此說道:「沒有人可以怪罪,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
家人中最能處理情緒的,應該就是我祖母了。她可以毫不掩藏地哭泣,恣意對陌生人訴說她的故事。每埋怨一次,彷彿痛苦就被洗刷清理一次。除了祖母,其他家人包括我,或許以為不去談論就可以讓傷口癒合,悲傷往事就真的過去了。殊不知被遮蔽的哀傷也許將凝滯在各自心裡,成為生命的負累。我要一直等到高中時談戀愛了,主動向初戀女友訴說這件事,悲傷才真正地流轉、挪移,多年鬱結才稍微鬆開。
為什麼我要比別的小孩堅強?
父親的葬禮,也是我童年的告別式。父親的靈柩停在外面,出殯那天許多人來送他。白色幡旗引路,隊伍浩浩蕩蕩,嗩吶吹啊吹,鑼鈸鏗鏗作響。我捧著牌位,披麻帶孝,並不真正清楚什麼是死亡。墓地位置就在村子外,距離不遠,葬禮結束後旋即徒步返回三合院家中。
所有儀式結束,一位父執輩蹲在牆角抽煙,招手要我過去。他神色凝重地對我說:「你已經沒有爸爸了,以後要更加堅強。」我說好,我知道。而「我知道」的意思,往往意謂著我聽見了,但我不一定認同也不一定做到。當時我賭氣地想著,為什麼我要比別的小孩堅強?是什麼讓我喪失快樂的權利?
真正悲傷的時候,只想要有人可以擁抱
勉人堅強惕勵的話語,在我成長過程中不斷出現。我必須很努力,才能掩飾對這種話以及說話者的反感。弔詭的是,我果真長成一個堅強又倔強的人,憑靠自己的努力去換取想要的生活。儘量不麻煩別人,不想擁有特別待遇,不收受任何人出於同情而安排給予的好處。如此說來,一個成年男人對剛剛失去父親的小孩說要堅強,或許還是有效果的。然而當我真正悲傷的時候,我最希望的是有人可以彼此擁抱,什麼都不用說。
那位長輩的訓示讓我茫茫然,不甚理解死了父親跟學習堅強的關連。我明白他沒有惡意,但某些自以為的善意,其傷害卻是遠勝於二手煙。說也奇怪,往後的人生裡,我未曾因為挫折橫逆而哭泣,反倒把自尊與自傲看得太過重要,常對自己對人生賭爛,形成性格裡的缺陷。那一天,父親入土為安了,天空是那麼藍,陽光是那麼燦爛,朱槿開得那麼漂亮,庭前芒果樹用力地開花結果……,然而七歲的我童年已經結束。〈天倫歌〉敘述的狀態:「人皆有父,翳我獨無。」我過早領略,也過早迎接責任。再過幾個月,我就要自己背書包去讀小學,靠著讀書改變命運了。
有時相當討厭自己的記憶力,該記的記不住,不該記的揮之不去。無法刪除的不快與哀傷,像趕不走的蒼蠅嗡嗡叫。童年裡的許多事件與細節我其實都記得,只是不願意說出來,也不願意讓人知道,我記得。現在似乎才稍稍明白,願意說出來的時候,或許可以不再那麼悲傷了。
摘自 凌性傑《男孩路》/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