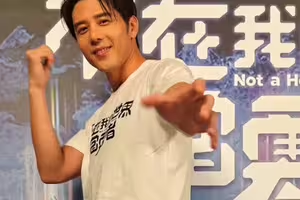針對發生在1950年代,軍方為逮捕疑為中共支持武裝基地成員,在位於新北市汐止、石碇交界的鹿窟一帶山區爆發台灣最大白色恐怖案件「鹿窟事件」,監察院19日通過監委高鳳仙、楊美鈴的調查報告並且糾正國防部,調查報告除對不當審判及感訓提出糾正,並指出當時軍隊強占民宅、肆意食用村民家禽、村民無故被毒打訊問,甚至還有部分村民淪為當時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的私人奴僕。

▲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耗時一年半調查鹿窟案。(圖/中央社)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民國38年9月間,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奉共黨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之命,在鹿窟地區建立基地並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後來基地改組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許多隊員是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受各種脅迫、利誘或矇騙而加入,但因為武器不多且性能不佳,隊員軍事訓練不足,因此戰鬥力相當低。
據調查,國防部自41年12月28日夜間起,派軍隊3800餘人至1萬餘人,對鹿窟山區展開圍捕,共逮捕及訊問896人,並由保密局在「光明寺」訊問,而且調查過程中對許多村民實施刑求,以木棍、藤條、槍托等毆打,並用針刺指甲、夾子拔指甲、灌水、倒吊,有人因為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或被打到骨頭破碎而發瘋,更有人於釋放後自殺,直到42年1月19日才撤離,根據許多村民控訴,期間還有軍隊恣意搜刮村民財產的情形。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當時保密局將231名案犯移送偵查審理,判決有罪93人(死刑28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64人),還有「以自新運用及感訓為名淪為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私人奴僕者19人」,前後時間長達1524天至2315天不等,造成後續冤獄賠償1億4800餘萬元。
根據調查報告,當年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法官審判時,未詳查被告是否有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等減刑事由、有無遭受刑求或受調查人員誤導、因不識字而不知筆錄記載內容,多僅憑被告的自白及共同被告陳述而為有罪判決,侵害被告人權,因為不當審判造成國家補償及冤獄賠償合計3億9400餘萬元。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本案調查費時1年半,曾向總統府、國防部等9個機關調取相關卷證資料共數百餘卷宗,赴鹿窟村現場履勘時,訪談當地村民及諮詢相關專家學者數十人,才提出長達600餘頁的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文,希望藉由這份國家官方調查報告,具有正向積極面對歷史的意義。
鹿窟事件,又稱鹿窟基地案,堪稱白色恐怖初期,台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將近六十年前,大多為礦工和農民的鹿窟村,雖然物質生活貧乏生活困苦,但時機混沌不明的戰後,與世無爭的兩百戶村民,彷彿像是世外桃源;只不過當二二八事件後,山下白色恐怖浪潮,終究湧上山頭,徹底改變了鹿窟村。
上萬軍警抓人 小村幾乎變刑場
1952年12月28日傍晚,一萬多名軍警悄悄摸黑上山,草木皆兵氣氛下,鹿窟對外道路全被封鎖。29日一早,剛出門的農夫、礦工,就一個個莫名其妙在路上被捕,立即被陸續送往充當指揮所的「菜廟」。被捕的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而冬天的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小廟還不時傳來哀嚎聲。

在之後風聲鶴唳的二十天期間,鹿窟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抓,許多被屈打成招的人,分批被送到市區監禁,等候軍法處審判,有人則被判死刑當場槍決。
根據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調查統計,當時鹿窟約有四百人被捕,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另外有近百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還有未成年兒童也被判坐牢,因受牽連的村民太多,形同滅村。
張炎憲研究顯示,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遭到阻礙,台共組織紛紛被破獲,部份成員於是先後進入鹿窟山區躲藏、避難。而共產黨員上山後,為了生存,向當地居民假稱是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以取得村民的同情協助,並運用當地親友關係,吸收村民加入組織。

呂赫若於1950至1959年,參與鹿窟事件而死難於石碇附近的鹿窟,享年僅三十八歲。
純樸無辜小村莊 一夕被控匪諜村
由於當地住民的教育程度不高,訓練參加者的方式多只是聚集講話,能夠真正瞭解組織及意識型態者幾乎沒有,因此更別說實際進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動作。只是,當國防部保密局取得密報後,動用一萬名軍警上山抓人,這些大部份是農民或礦工,多數未受教育的父子、父女、兄弟等純樸百姓,卻在政治風暴中蒙冤受難。
許多後來研究結果指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也不是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查獲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少數土製手榴彈,則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回來,將其稱為「武裝基地」實在勉強。
當年噤若寒蟬的「鹿窟事件」,基本上是「二二八」的延續;躲進鹿窟山區的人,雖然有可能是官方所認定的共黨份子,但也有可能只是左傾知識份子,或者更只是「二二八」的避難者。當中有些人或許搞組織,但完全沒證據顯示進行過所謂的武裝基地。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鹿窟村民都是無辜,只因身處那樣的年代,就承受了如此莫大的苦難。
二二八延伸的鹿窟事件,人們其實並不清楚那年鹿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今日的鹿窟紀念碑文寫著:「今日立碑,除追悼冤屈,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至於,真相與教訓能否清晰,就如常年雲霧的鹿窟山區,恐怕還得再等待。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與《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書封,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李石城回憶錄的重要性
張炎憲教授(1947~2014)主持的鹿窟事件口述歷史計畫,分兩次出版:第一本是《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高淑媛,台北縣文化中心,1998),第二本是《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張炎憲、陳鳳華,台北縣文化中心,2000)。若非當時台北縣是民進黨執政,且其文化中心主任恰好是對台灣史相當熟悉的劉峰松,或許這樣的計畫根本不會存在;因為口述歷史的執行繁瑣費時,以第一本30個受訪者、第二本40個受訪者的工作量,若非張炎憲的苦心及遠見,恐怕亦非一般文史工作者可能承擔。
2015年2月,鹿窟事件受難人李石城出版了《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2015),近400頁的大書,更將讀者帶回1952年前後鹿窟事件的原始時空,深入揭露了特務橫行之下,鹿窟附近村里中老少男女被株連入獄的悲慘經過。或許由於台灣政治風氣逐漸開放,人權保障較受重視,以致李石城可以放膽的寫出他們被訴、被關期間特務們種種違法、背德的迫害細節,其中最令人義憤的,就是他記錄了自身屢次遭刑求的方式;反觀張炎憲兩本口述歷史,受訪者雖多少論及刑求,卻心存顧忌,支吾其詞,由此可見特務文化對他們的殘害之深,即使事過境遷,他們仍活在歷史的陰影下。
李石城在鹿窟事件爆發時才17歲,因為遠房表哥陳春慶(後來所謂的「共產黨徒」)山上的房子,曾提供給一些左派的朋友長期居住,他常被叫去跑腿買些日用品及食物,牽連被捕。起初,他從家中被架到水窟頭,一個兵把綁腿解下來,當做繩索把他雙手扭向背後,緊緊綁住,再接一條長繩,像拉狗一樣拉著他,走到外厝的公廳(就是廖論、廖賜的家),那裡駐有一連兵,連部設在廳內。有個軍官問他陳春慶躲在哪裡,他回答不知道,那軍官立刻撂很話:「你要認清楚,現在的你比一隻螞蟻還不如,我要你死,你就活不了……要死要活你自己選擇,我保證你隨時可以回家,要不然就別怪我不客氣!」
李石城再回答不知道,軍官便命令兩個強壯的兵,把他臉朝下,綁在長板椅上,就地取材,拿起廖家鋸成的四尺長、放在門邊本來打算做斗籠的十多段桂竹,兩個兵一人各站一邊,死命往他身上抽打,不停歇的打,竹子裂開再換新的,那軍官還一直發出獰笑聲,「怎麼?滋味如何?這是最初段,你有興趣,我再變幾個花樣給你嘗嘗,不用急,先把他放下來。」
當李石城從長條椅滾到地上時,已動彈不得,雙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完全失去知覺。他真的不知道陳春慶到哪裡去了,軍官再問他又照實答,軍官就說:「王八蛋,我要看你是銅打的還是鐵做的。」接著指揮一個兵把李石城按跪在地上,拿一根竹子放在他的大腿與小腿之間,用繩子把大腿與小腿綁緊,然後兩個兵分站在竹子的兩端,不斷的滾動竹子,連續一小時,李石城不但汗淚如雨下,連尿都被逼出來了,然而他還是說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軍官就命令兩個兵把他拉出去斃了。李石城半跪半癱的,只聽到轟轟兩聲槍響,一陣耳鳴,卻沒有中槍。
威脅槍斃還不講,軍官要那兩個兵把李石城架回屋內,臉朝天,綁在長條板上,旁邊有兩座石磨,上座有50公斤、下座至少200公斤,軍官叫兵抬來上座,壓在他肚上,再以繩索綁定,使他呼吸困難,從近午夜到第二天凌晨4點才放他下來。那天是1953年1月9日,距離特務包圍鹿窟一帶已12天。天亮之後,李石城被一個兵扶著,走到10分鐘之遙的菜廟(今天的「光明寺」),半路上,已聽到廟內哭號不斷,許多人在呼天喊地、哀爸叫母,一聲比一聲淒厲。到菜廟之後,和大夥兒相聚,才多少知道這陣子被捕的村民無數,一批來一批去,都被整得很慘。
李石城被要求蹲著,因為腿傷劇痛,也只好半蹲半坐,熬過了在菜廟第一天。第二天來了個胖胖的特務,起先還和顏悅色,眼看問不出名堂時,突然以右手用力握住李石城瘀血的大腿,並迅速以雙手在他傷痛的大腿揉來搓去,用力捏個不停,以致他痛得滾地哀號,尿失禁了一地。胖特務這時說:「我是好心幫你活血,不然血凝太久,你的雙腳是要報廢的。」看李石誠還是說不知道,便命令兩個兵一邊一個,將他雙手的大姆指以繩索綁緊,將繩子甩過橫樑,用力拉到他的雙腳只有腳尖一半著地。胖特務要兵好好看著李石城,如果肯坦白說再放他下來;李石城就這樣從早上11點吊到下午3點,胖特務又出現了,叫兵把李石城放下來,去吃吃飯好好反省,這時,李石城的兩根大姆指幾乎失去感覺,連筷子都拿不起來。
 《鹿窟事件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出版。
《鹿窟事件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出版。
1953年1月21日,大夥兒被押上軍車,送往當時被台灣省包安司令部佔用的台北市萬華的東願寺。1月28日,李石城被押去地下審問室,問不出來,6個人把他騰空架起來,頭下腳上,「當我的頭浸入水裡時,一下子水灌進鼻孔,隨呼吸進入肺部,這時真是到了臨死前拼命掙扎的程度,但掙扎無用,他門四個大漢用力抓住我的四肢,把我的頭硬插進水桶,初進水桶非常痛苦,只知道自己尿都滲出來了,不久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他們嘻笑的問我滋味如何,還要再來一次嗎?」
3月7日,再拷問。兩個人把李石城的手臂夾向背後,用繩索綁住雙臂,把繩索翻過橫樑,用力把他拉到離地兩尺高,像吊粽仔般的,懸在空中,一邊站一人,一直用力推。他們「讓我像鞦韆一樣不斷擺動,靠雙臂要負載整個人的體重已非常痛苦了,再經他們不斷的推動,兩臂像要斷掉一般的難受。他們一邊喝茶一邊談笑,好像看我受苦可以助長他們的樂趣似的……」這樣還是說不知道,兩個人於是改綁李石城的雙腳,讓他顛倒過來懸盪,「這樣人的血液全部灌進腦部,頭像要炸開、暈眩,要吐又吐不出來,心臟跳得連自己也聽得到,真是到瀕死的程度。」大概他們也知道這樣會出人命的,不久後放他下來,這時他連站都站不住。
李石城一直說不知道,審問人士便把他的右手挾在後面,綁在椅子靠背上,身體和腳都綁好,只有左手沒綁。他們拿來一條毛巾,在他的左手掌繞兩圈,只露出四根手指頭,然後將他的左手放在桌邊,讓四根手指頭伸出桌邊半寸左右,再以一塊約二尺長的木板,壓住他左手兩頭綁緊,使他的手無法移動。「有一個人拿了一碗酒放在我的面前,再拿一個有蓋的鐵罐,故意搖動讓裡面的東西因碰撞發出聲響。」審問人坐在他面前,打開鐵罐,拿出四支鋼針,比一般縫衣針略粗一點,每支約寸半長。「現在坦白還來得及,再5分鐘就沒人救得了你,快說!」
審問人員見李石城沒有反應,便拿一支針沾點酒,刺進他的中指指縫約三分深,再從衣口袋掏出鋼筆,慢慢敲著針頭,讓針深入他的指頭。李石城無話可說,審問人員便給他無名指再插一針,當他痛得尿失禁時,審問人員取笑他:「你水喝太多了。」李石城說:「給我死吧!」審問人員回答:「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想死還早得很,你不說,我就再給你一針,看你硬到什麼時候。」但他那針並未插下去,只是每隔幾分鐘,就拿鋼筆敲敲插在他雙指縫的針,痛得李石城冷汗直流,內衣濕透。這樣逼供一個多小時,近午飯時間才放他歸營。
回到營裡,難友都為李石城煩惱,也安慰他,有人被連插4針,插2針算是好運的。「我用一雙發抖的手拿飯想要吃,太痛就又不想吃,耳邊突然想起慈母的聲音:『城啊!你三頓著吃乎飽。』不覺淚流滿面。難友問我是不是很痛,我說當然是痛,不過現在我是想起老母在家無飯可吃,才傷心落淚……」
後來李石城被送去好幾個地方,回到保安處,已是3月27日了,又被叫去審問室,牆角放著一桶青色的水,統內有一支泥水工洗石仔的手壓式壓水器,審問官告訴他,這叫做「洗腦機」,「你想了那麼多天,想清楚了嗎?趕快坦白,不然動用洗腦機,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李石城不招,審問官便要兩個大漢把他綁在長條椅上,臉朝天,四肢綁在長椅的四角,頭固定住,他們把軟管插進李石城的鼻孔,開關一打開,一股強力水柱直衝腦門,腦內像萬蛇滾動,幾乎無法呼吸,話也講不出,屎尿都拉在褲檔裡,一陣暈眩,他就昏了過去。醒來時李石城發現有兩個人在壓他的胸口,一邊說:「真是沒用,一下子就暈倒了!」

自認為國民黨超級特務的谷正文。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谷正文將19人收為奴工
直到1955年7月4日,李石城才被判刑,罪名是「參加偽匪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一般案件都半年左右便定讞了,但鹿窟案當初涉案人數有200多人(當場打死1人),超過2年還沒有宣判的,還大有人在。最後槍決者35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刑期合計865年。最荒謬的莫過於19人(男13人、女6人)未依法定程序審判而被違法拘留,谷正文留下他們做為差遣、家傭及跟監等之用,時間長達5、6年。
根據張炎憲的口述歷史記載:陳燕、陳桂在谷正文妻的住處幫忙洗衣、煮飯、帶小孩;陳寶珠、陳金土被派出跟監;高泰被派去五股挖魚池、砍竹子、圍籬笆;鄭定國做木工;李天池負責養雞;廖水塗、高有土被派區桃園看顧埤仔;陳久雄替谷正文倒茶、拿公事包。他們都必須做雜役和打掃,並照顧谷正文兩位妻子的生活。在口述記錄中陳燕說,她在谷正文家中幫傭,白天忙廚房的事,半夜兩三小時就要起來幫谷正文初生的嬰兒泡牛奶、翻身、換尿布等,有幾年每天只能睡2小時,還好年輕,不然怎麼撐得住;偏偏谷正文家中人口又特別多,他妻妾成群,其中兩位老婆是姊妹,大老婆有3男1女,小老婆有1女3男,小孩又常生病,被非法留置的6名女子,就一天到晚服侍他們,忙得天翻地覆。
陳寶珠則在口述歷史中說,八德血案發生後,國防部一位情報組長一家五口被殺,為了破案,他們被派去晚上住他們的房子,找來招魂師,看看那些冤魂野鬼會不會附在他們身上,講出兇手是誰,後來不了了之,但他們都嚇壞了,又不敢不從。此外,谷正文手上有一大本名冊,是當時審問記錄抄來的,沒事時就會根據名冊,帶這19個「奴工」去明察暗訪。谷正文脾氣很大,動不動就說:「你們不聽話,通通給你們送外島,一個一個抓起來槍斃。」但谷正文也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因此每逢上司到他家,這19人就必須集中關起來,不讓上司看到,後來被其中的廖有塗寫信檢舉,谷正文才不情不願的放了人。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明白寫著:「當時社會狀況還是亂得很(註,指二二八事件後的4、5年),保密局內部也被蔣介石全力肅清武裝基地的指示給弄得焦頭爛額。不過,據我個人的看法,這些武裝基地,實在是毫無武裝規模可言…只是在破獲竹仔坑基地之後,行動就不得不持續下去。」在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循線破獲台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並在該部書記溫萬金家裡,找到一本日記,記載了他在那年4月至6月間的受訓情形及見聞,「保密局內部認為,這是個極具規模的武裝基地」,經過調查,鎖定石碇至汐止間的鹿窟山區,當時的衛戍司令張柏亭估計,以每50公尺1人計算,大約需要一團兵力,後來經會議決定,再增加一個加強營協助,在那年的12月28日展開行動。行動的總指揮就是谷正文。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在網拍上仍奇貨可居。獨家文化出版。
 |
| 溫萬金在行刑前,曾以毛巾包覆石塊攻擊獄卒,最後慘死刀下。(溫世動提供) |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說,當天他們抓了600多人,谷正文為了過濾,找了所謂「基地的資深幹部」汪枝來,那些人一個個從谷面前經過,汪枝就站在谷正文看得見而那些人看不見的氣窗後,「如果這人是台共成員,你就把手放在窗台上,如果不是,就把手收回去。」谷正文吹噓說,十來個人經過之後,簡直把他視為「神探」,「就再沒有人喊冤枉了,只是眼裡流露著驚惶的神色,安靜的默認一切……」這就是當年保密局辦鹿窟案的「偵察方法」。接著,谷正文認為有嫌疑的200多人(其中包括60多個像李石城這樣16、17歲,沒受過教育的大孩子),陸續帶到菜廟裡或其他處所集中,個別施以審問及拷打,有的還強迫畫押承認「犯行」。至於如何審訊,前面引述的李石城回憶錄,可以當做重要參考;大多數人一生知道的別人名字,就是親戚鄰居的名字,若禁不起刑求,便有人要倒楣了。
這200多人來自石碇鄉鹿窟村、汐止白雲里、汐止東山里、汐止佳冬里、瑞芳、玉桂嶺及台北市南港一帶,可說鹿窟相關山區的青壯年男丁為之一空,只留下孤兒寡母在家,他們原多是採礦或兼務農為生,很多家戶是父子、兄弟姊妹、夫妻、表親同時被抓、被關、被刑,甚至同死;受難者離家就審、服刑期間,造就了無數破碎的家庭。多年後能夠幸運返家的受難者,因為多半教育程度有限,只好再度下礦坑或務農,但身體已在刑訊過程中折損了,刑餘之人,早死者不在少數。
那麼,大家或許會問,是不是當年真的有所謂「一堆匪徒在鹿窟山上基地升五星旗」的事?據自首參加匪組織的陳旬煙口述:「山上升五星旗是真的,宣誓時唱那邊的國歌,也有小組會議、精神訓練,由指導員講課較多,也分發小張綱要,利用晚上或大清早集會。」但至於山上究竟曾有多少所謂「匪徒」聚集?曾謀反什麼?那些判了35個死刑、865年有期徒刑的所謂判決書,可就什麼都講不清楚。
鹿窟案唯一蒐獲的所謂「物證」是:大小五星旗6面、五星臂章10條、人民武裝保衛隊旗2面、軍用地圖43幅、駁殼槍1支、收報機1具、手銬1付、反動書籍及匪文件55冊。連谷正文都說:「嚴格說來,整個鹿窟對國民黨並無太大實際價值,但是在象徵意義上卻頗為重大。」這是什麼意思呢?講白話,就是株連甚廣,殺雞儆猴,讓台灣的農民有所警覺,不要再在山上藏什麼「反動組織」了。
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是政府在鹿窟設一塊紀念碑就夠了。發給受難者或其家屬補償金,亦永遠無法撫平他們心中巨大至深的傷痕。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轉型正義,畢竟要告訴大家一些故事緣由,讓大家看到一些加害人的姓名,才多少能滿足大家的正義感。
 鹿窟事件受難者刑期表。資料來源:《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
鹿窟事件受難者刑期表。資料來源:《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


 首頁
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