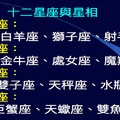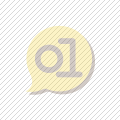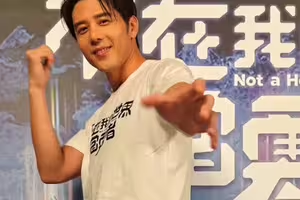在朋友的眼裡,我是典型的幸福女人。丈夫皓傑從機關下海,正趕上房地產市場迅猛發展,幾年間就成了成功人士。我自己大學畢業後留校,作為優秀青年教師的典型破格晉升職稱,成為了學院最年輕的心理學教授。同事和朋友都說,活到這份上,你算得上是“五星級”女人了。
可是,我沒想到自己平靜的生活會被一次平常的講課激起水花。那次,市公安局請我為刑警們做一次女性心理學講座。講課的間隙,我發現台下有位中年男子,一直不錯眼地注視著我,一旦和我的目光相遇,他就微笑著略略點點頭。後來我知道,這個人就是屢立戰功的刑偵隊長趙鵬。
當晚,公安局辦了一桌酒招待我,不勝酒力的我應接不暇。觥籌交錯之中,坐在我對面的趙鵬用手指夾起了兩隻酒杯,趁別人不注意向我點了點頭,然後自顧自地斟滿酒一飲而盡,他就這樣接連喝了三次,一共六杯酒。那晚我和趙鵬沒說一句話,但作為成年人我們彼此都清楚,對方已經注意到了自己。
一個月後趙鵬打來了電話。我當時正伏案寫講義,想起他那奇特的敬酒方式,忍不住笑出聲來,這一笑馬上拉近了兩個人的距離,也給我們的交往定下了輕鬆的調子。聊天時,他開起玩笑特好玩。趙鵬興奮的時候會說:“何教授啊,再給我們講一回課吧,哪天我去娶你?啊說錯了,是去接你。”對他這種小小的把戲,我並不住心裡去,男人嘛,嘴上總是要占點便宜的。
一天,趙鵬打來電話,說我那次講座啟發了他的思路,一起陳年舊案剛剛偵破,得了五千元獎金,要請我吃飯。我收住笑,鄭重地說“趙隊,我不想找什麼藉口,我不能去也不想去”,而且我頓了頓又說,“我以後也不會赴這種飯局。”
趙鵬沉默了一會兒說:“對不起。”然後輕輕地放下了電話。
我記得一句話在適當的時候,人應該插上欲望的門閂。我對幸福的理解是丈夫、女兒和事業,至於別的快樂,我認為都是不會長久的。我以為和趙鵬的交往到此就該結束了,惆悵幾天後就會漸漸淡忘了此事。
早春的一個陰雨天,我正看著窗外發呆,趙鵬主動打來了電話:“你好嗎小何?”我心裡暫態灑滿了陽光,失而復得的快樂讓我興奮不已,我調皮地說“隊長,我以為你失蹤了,差點就要去報案了。”
一來二去,兩人又恢復了從前的關係,說話也漸漸隨便起來,問候語和結束語不時穿插著一些情人間才有的甜言蜜語。我漸漸習慣了這些。我不得不承認,和趙鵬交往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這樣一個異性知己也未嘗不可,反正自己不會和他見面,不會做出什麼過分的事。
(二)
2005年夏季,全市開展了一次掃黃打黑行動,可從頭至尾,晚報上的報導都沒有刑偵隊長趙鵬的名字。想想趙鵬已很久沒有電話,我把電話撥了過去,手機不開,辦公電話也沒人接,我心裡突然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8月初的一天,我去市檢察院找一個同學,忽然聽到有人提到了趙鵬。我急忙問同學:“趙鵬?——怎麼這名字聽著這麼耳熟呢?”同學壓低聲音說“他是公安局刑偵隊長,剛被撤職,聽說要查他,弄不好得關進去。”我的心頓時如刀剜一般的疼。我無法想像,傲氣、自信又倔強的趙鵬此時會是什麼狀況?
此時,皓傑去南方出差,6歲的女兒去了奶奶家,我一人在家裡沒日沒夜地撥打趙鵬的手機。我固執地想,無論他在哪裡都要找到他,就算他真進了監獄也要去看望他,他曾經給自己帶來那麼多的快樂,現在他落難了,自己絕不能袖手旁觀。
一個深夜,手機突然通了,那長長的靜候音讓我緊張得心怦怦直跳。終於,趙鵬略帶沙啞的聲音傳來了“我,是你嗎?”
我激動得聲音都有些顫抖了,“趙鵬,你為什麼不開機?”趙鵬有些落寞“事情還沒結束,許多人都打電話來問,不想接,只好把卡換了。今晚閑著沒事又把原來的卡換上了,沒想到這麼巧,你的電話剛好就進來了。”“我剛看完電視,閑著沒事就給你撥了一個電話……”我沒說實話,她不想讓趙鵬有被人可憐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