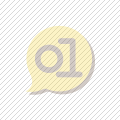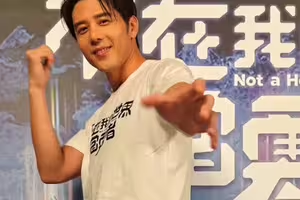雨夜的身體是光亮的
「嘟嘟,嘟嘟嘟」。像是指尖在叩門,這是我設置的Out Look收到郵件時發出的聲音。電腦屏幕上一個等待開啟的信封圖標在不停閃爍,看了一眼E-mail地址,我知道,是孟萍發來的。
2010年2月14日,情人節。武漢依然春寒料峭。窗外飄著凄冷的雨,當然,我所在的湖北經濟電視台辦公樓里有暖氣,可是沒來由地,從看見郵件的那一秒鐘開始,我的手不停抖動。
孟萍是我的女友,起碼這一秒鐘和這一秒鐘之前的8年時間裡,她是。然而她已經有三個月沒有給我任何訊息了。
挪動滑鼠,公文一樣黑白分明的字鋪滿了屏幕,哪有舊時展讀信箋的怦然心動?我一字一字地看信:
「親愛的越,武漢的2月一定非常潮濕吧,這時節加拿大的楓葉美極了。這封信早想寫了,相信我,我和你一樣內心天天都在受著煎熬。元旦那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驅車去了多倫多市中央公園的湖心島,有焰火晚會。當耳邊傳來禮炮聲、爆竹聲和隨著哨鳴飛向天空的茲茲聲時,身旁有人為我送上了玫瑰。我拒絕了他。從那天開始,我的2007年在他每天一束玫瑰的包圍下度過。現在這兒正是深夜,可窗外霓虹閃爍,夜空繽紛。熱鬧繁華的背後,我覺得自己太孤單了。所以,原諒我……」
孟萍的文采還是這麼漂亮,哪怕寫分手信都講究美感,我的嘴角浮起一絲嘲諷的笑,心裡卻錐穿一樣痛。
頭兒在那邊喊我的名字,讓我趕緊扛起攝像機出發。我木然地答應了一聲,關頁面、關郵件、關電腦。下意識里記得的最後一個動作是刪去來信,順便也將這個郵件地址從「聯繫人」一欄中永久刪除。
晚上11點半,採訪車將我丟回到電視台大門口。沒有傘,我站在武漢的雨夜裡發獃。電視台大樓外是藍色的玻璃牆,吸取著、反射著、交織著各種各樣的霓虹燈光,然後呈現海一樣的深藍色。
不遠處就是我的單身宿舍,可我不想回去。我揮手招了一輛的士:「去漢口,找家最熱鬧的酒吧。」30分鐘後,我坐在了漢口「紅色戀人」酒吧里。這是個光怪陸離的去處,這是個聲色犬馬的場所,誰都不認識誰但滿眼看到的都是人,什麼都聽不清但耳朵里可以塞滿聲音,我縮在角落裡看沸騰的舞池。我已經在喝第四瓶啤酒了。
突然音響里爆出一聲禮炮般的聲音,然後是模擬煙火射向天空的哨音,舞池上方的燈隨之變幻出五彩的光,煙花從夜空凋落飛散灑到每個人的臉上。
一切都在對我散發著蠱惑的光亮。這是個美妙的夜晚,一個有故事的夜晚嗎?
故事來了,來的這個女孩有一張嫵媚的臉,濃墨重彩地化著夜妝,塗著鮮紅光澤的唇。她一定已經喝得很多了,用又高又深的玻璃杯裝著干紅酒,擠到我身邊坐下,拿過我面前的啤酒,倒進一些在自己的紅酒杯里,然後說:「乾杯,為我不認識你。」
我笑起來,搶過她杯里的混合酒,倒一半在我的杯子里,喝了。味道倒有些特別,我從來沒覺得自己這麼敏感過,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伸手去摸女孩的臉龐,她有一雙令人心疼的眼睛,霧一樣雨一樣。
女孩開始笑:「你一定失戀了。女孩出國了,或者當人家二奶了。」
我也笑:「怎麼那麼俗套啊,那你呢,是不是一樣的?」女孩突然貼在我的耳邊,聲音充滿了古怪的誘惑,挑逗的話語並不熟練,但的確很誘人:「我可以吻你嗎?」
我拿不準自己該怎樣繼續,心頭有面旗幟被風吹開了一角。突然腦海里浮現出孟萍的樣子,彷彿看見她仰臉望向加拿大的夜空,一臉陶醉。我咬著牙拚命搖頭,想將她的樣子甩出去,這時女子的舌尖掠過我的耳畔:「全都忘了吧。」彷彿咒語一般,孟萍的身影消失了。摟緊眼前這個不知名的女子,我心裡煙花滿天。
她的唇野蠻地侵略過來,狂風驟雨一般,柔軟濕潤--溫柔的暴力。我將眼睛閉上了,眼前卻是炫目的光芒。是什麼煙花照亮了這個黑夜,是什麼潮汐在拍打心海,又是誰,如同度身訂做一般地吻著自己?
說不清誰摟著誰誰扶著誰離開了酒吧,說不清這個瘋狂愛了一宿的房間屬於什麼酒店,也說不清燈有沒有開天又是何時亮的。我醒來時女孩已經離開了,只是在一個可能她忘記拿走的手提袋裡,我看見一套嶄新的化妝品,還有一副眼鏡。女式眼鏡,舊的,很老土粗笨的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