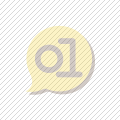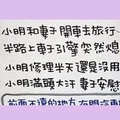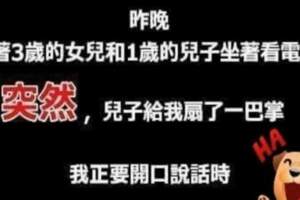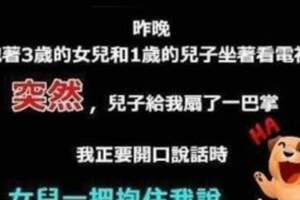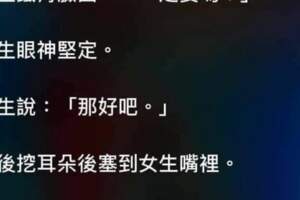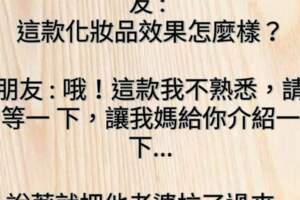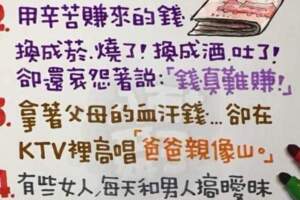這些天,時常想起小時候跟農民五叔學英語的一些往事碎片。
老家在桂粵交界處,粵語是母語,因為香港的緣故,粵語中摻進了不少英語外來詞,比如,把打球叫打波(ball),把果凍叫者哩(jelly),把襯衫叫恤(shirt)衫,把小甜餅叫曲奇(cookie),把公共汽車叫巴士(bus)等,不勝枚舉,哪怕目不識丁的老太太也這樣叫,不能不讓非粵語區的人感到驚奇。
我接觸英語的時間很早,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還未上學,出於好奇,就開始跟當農民的五叔學習英語了,學的第一個單詞是「惡過偷伯」(October十月),學的第一句話是「狼來扯棉帽」(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萬歲),此後,在五叔糟糕的發音的指導下,一路忘乎所以地學下去。
五叔發音不準,其實不能怪他,他的英語差不多都是自學的,五叔學英語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批判英帝國主義,當時,在中國大陸民眾的潛意識裡,俄語和英語似乎涇渭分明地分屬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因此,學俄語的人趨之若鶩,學英語的人寥若晨星,偏偏呆在香港的番鬼佬(英國人)不安分,經常放飛各種攜有傳單的氫氣球,氣球在空中爆裂後,花花綠綠的傳單就隨風撒得到處都是。當時六井大隊有令,凡拾到傳單,必須上交大隊革委會,藏匿傳單者一律與偷聽敵台者同罪。可傳單收上來了,上面的雞腸字(英文)是什麼意思?番鬼佬是怎麼罵我們的?為了知己知彼,大隊支書就把學習翻譯這些雞腸字的任務落到了我五叔的頭上。
五叔當時是六井中小學的語文教師,民辦。為了早日把民辦轉為公辦,他就把這一艱巨任務承接了過來,可是不會發音,怎麼辦?五叔像老虎吃天一樣無從下口,後來他突發奇想,把英語當作拼音來認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於是他就發明了漢字注音法,比如,fan(球迷)注音「煩」,angle(角度)注音「昂樂」,adequate(足夠的)注音「阿德娶阿特」,anticipate(預料)注音「俺提此怕特」,等等,這樣注音,倒是容易把單詞記住,可發音卻相去十萬八千里,五叔想,反正又不跟那些傳單對話,發音準不準確都無所謂。
兩年後,村裡來了一個姓詘的牛鬼蛇神,老詘原是縣中學的英語教師,學校改教俄語後,老詘無所事事,經常收聽敵台,甚至還有一次,他在朗誦一篇英文小說時,居然膽大包天地說了句「東怕尼克松」(Don』tpanic,son.別慌,兒子),遂被革命師生打倒,下放到六井大隊來挑大糞。五叔的英語發音,常令老詘噴飯。老詘對五叔進行糾正,無奈五叔積習太深,收效不大。
五叔教我學英語時曾經說過,番鬼佬最大的特點是喜歡說反話,明明是李同志,偏偏要說成同志李(ComradeLi),寫個信封,地名不是由大到小寫,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讀音也常常是正話反說,明明是播種(sow),卻要發「收」音,明明是受苦(suffer),卻要發音「舒服」,明明是廚師長(chef),卻硬要把人家叫成「車夫」…….
五叔承認粵語中有不少英語外來詞,但出於愛國,他也試圖從英語中找出儘可能多的漢語外來詞,typhoon(颱風)mango(芒果)mandarin(滿大人)自不必說,就是coolie(苦力)unty(阿姨)muffled(模糊)這些原汁原味的英語單詞,因為發音跟漢字有些相似,五叔也堅持說是從漢語譯音化來的,幸虧沒有英國人為版權問題找他算帳。
五叔翻譯傳單,愛用直譯,有時甚至還望文生義,比如,dead除了有「死的」之意外,還有「很」的意思。五叔有一次把youaredeadright!(你很正確!)翻譯成「你死得其所!」像這樣的誤譯,在五叔保留下來的翻譯底稿中屢見不鮮,因此,常把支書看到火冒三丈,邊看邊大罵番鬼佬鬼話連篇。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五叔的轉正問題一直沒有著落。
我大學畢業那年,六井村銅鼓堡作為太平天國的古戰場被當地開發成廣西著名的旅遊景點,常有不少外國人從香港、澳門等地前來觀光,五叔的公辦教師夢徹底破滅之後,他就辭去教職,當起了導遊,他那糟糕的英語發音常把老外逗得哈哈大笑,因為老外中有不少人都懂漢語。
我每次回老家探親,看到五叔時,都要習慣地問候一句:「Howdoyoudo?」(你好嗎?)
五叔的回答照例是中西合璧的,他說:「你do我也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