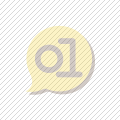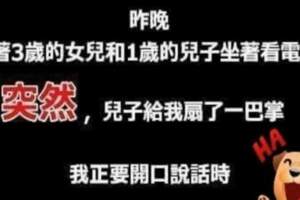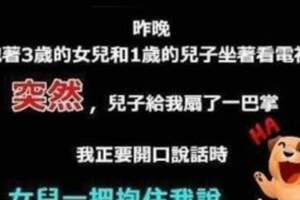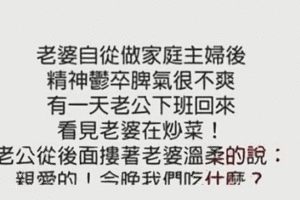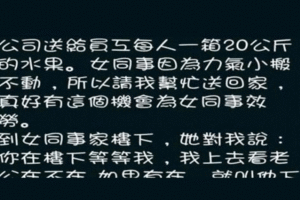這事兒我不信,說破大天我也不信,講給你聽,你肯定也不相信。
有天晚上和趙亮在「夢幻」餐廳小酌,趙亮忽然指著餐廳對面的一座樓說:「你知道那座樓是誰的嗎?」
我問「誰呀?」
「就是咱高中同學吳春,他可發了,成大款了。」
「哦!是他!」我把舉杯的手停在半空,嘴巴成O型,驚訝之後頭搖得象撥浪鼓兒。
我不解地問:「趙亮你是不是喝多了,腦袋發熱,把笑話當真事。要聽笑話,我來,隨便講一個準讓你做夢都想笑。前幾年吳春還在街里蹬「板的」,怎麼可能這麼快掙得下這幾十萬元的樓呢?是撿了金條還是搶了銀行。
趙亮仍一臉認真樣:
「你別不信,現在稀奇古怪,出人意料的啥事都有;什麼克隆羊,雞蛋長把兒,柯林頓性醜聞……讓你屢見不鮮,見怪不怪。」
「克隆是生物學的貢獻;雞蛋長把兒報紙上見過,是雞吃飼料的複雜反應;關於柯林頓性醜聞,不敢妄論;要說馬季下蛋,我相信,那是編故事逗人樂的。」我調侃地說。
趙亮說這不是編故事逗你開心。我問那是怎麼回事,總得有點情節過程說出來讓人慢慢接受吧。
吳春是我和趙亮的高中同學,畢業高考名落孫山,父母無錢無勢吳春只好蹬板的自謀出路。因他長得瘦小臉黑,加之沒有職業,三十齣頭才取妻生子,後來我們忙於工作就來往甚少。不過前幾年我的確見他還在街里蹬車的呀,他怎麼可能這麼快成為富甲一方的大款呢?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吳春有個鄉下的舅丈么?」
「舅丈?」趙亮跟我賣關子顧弄玄虛。
我說,「你編的夠玄的,怎麼又扯出個舅丈,快湊足一部長篇了。」我耐著性子聽,看他怎麼收場自圓其說。
「花開兩朵,各表一支,話說……」趙亮幽默地用了講評書的開場白。
吳春的舅丈(舅丈是妻子的娘家舅舅),並非傳奇人物,只不過是位赤腳醫生。這在鄉村是很吃得開的行當,鄉里鄉親,有個頭痛腦熱的東家求西家請,有錢的就給點,沒錢的秋後給糧食。所以舅丈家不缺東少西,日子過得挺滋潤,唯一遺憾的是膝下有女無兒,空有一身醫術沒法流傳。
「話說這年正月飄雪的一天,吳春抱著剛滿周歲的孩子,跟妻子去鄉下給舅丈拜年。舅丈正盤腿坐在炕上呷酒,見這一家三口頂著風雪凍得抖成一團,趕緊讓到炕里又加菜又熱酒,吳春飢寒耐寒,自顧吃喝起來。舅丈細端又黑又瘦的吳春,看看外甥女不堪入時的打扮和懷裡嗷嗷待哺的幼兒,料定他們在城裡的日子過得困苦,不免生出惻隱之心,想把醫術傳給吳春,一是幫他們把日子過起來,二是為了自己的醫術後繼有人,便試探他是否願意留下學醫。吳春早蹬膩了車自然滿口答應。於是他便跟隨舅丈走東村竄西村,行醫賣葯,兩年下來學滿師成就回到城裡開了一家診所。誰料他從此大發特發起來。」趙亮講完自鳴得意地望著我。我仍一頭霧水,相信裡面還有許多疑問,但一時找不出便問:
「這麼說吳春是位手到病除的名醫嘍,他治療什麼樣的疑難雜症呢?」
「祖傳秘方,專治性病。」趙亮壓低嗓音。
我和趙亮相視大笑。象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大多以事業和家庭為重,所以常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的,難得暢快地大笑,輕鬆地放縱。且不管他故事的真假,吳春是否發了,只為這開懷一笑乾杯!那個晚上,我和趙亮喝得酣暢,連吳春是誰都記不清了。
但這並不影響事情的發展。吳春綻露頭角逐漸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是緣於他挨家挨戶散發的廣告。當然在我們家門縫同樣「有幸」夾裹著一張,上面還有他放大的彩照。這時全城的人包括我才重新認識他,我拿著廣告宣傳單端倪良久,回想當年書生氣的同窗,又黑又瘦街里蹬板的吳春和現在西裝革履專治性病的名醫、專家怎麼也聯繫不到一起,這真的是我的同學嗎?我既懷疑卻又希望,這一切如果是事實,我還是不敢相信。
時隔多日,我和趙亮又相聚在「夢幻」餐廳,趙亮風風火火的說:
「你聽說了嗎?吳春出事了。」
「出了什麼事,難道也像馬季下了個蛋。」
「這回可慘了,他給人家治病出了事故,被告上法庭判了刑,還沒收全部財產,哎……」趙亮憐憫起吳春的遭遇。
而我不得不說,這樣的結局才合乎情理(不是幸災樂禍)。因為他的命運里充滿著離奇的機遇,偶然的巧合。以至於他糊裡糊塗,辨不出是非,不去求真務實反而吹捧自己是名醫、專家做著發財夢想。早應料到會有慘敗的那一天。他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富有,那隻不過是黃粱一夢。所以任你怎麼說我沒有相信
「那就為吳春的故事乾杯吧!」
趙亮舉起杯,這次我們都沒笑。
「夢幻」餐廳對面的那座樓已裝修一新,更換新主,過不了多久,又將有一家公司開張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