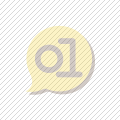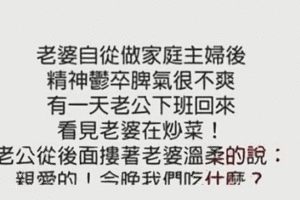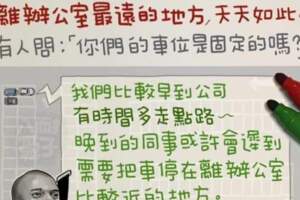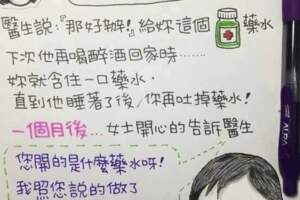A。一朵花兒開,就有一朵花兒敗
我撥通路藍的電話,問:「你能原諒我嗎?」她很用力地罵了句「神經病」,就將電話掛斷了。
美蓮打我電話,聲音滄桑,問:「你能原諒我嗎?」我想罵神經病,卻罵不出口,然後,電話也掛斷了。
連續下了十幾天的雨,今天突然轉出一輪晴日來,我隱在咖啡廳的角落裡,看著陽光如碎金似的散落在地板上。
如果是和路藍來,我一定會選落地玻璃窗旁邊的位置——因為那裡有明媚的陽光。對一個正處於秋寒季節的城市來講,坐在陽光里,已經是種絕妙的享受。
可是今天我不能坐窗邊。原因其實很簡單:來赴我約會的,不是路藍,而是美蓮。
路藍是我的妻,而美蓮,是我的「曖昧」。每個男人的生命里都會有兩朵玫瑰,一朵白的,一朵紅的。很不幸,路藍成了我的妻,所以她不是床前「明月光」,而是地上的霜——看上去純凈,卻讓人覺得冷。
淺啜著咖啡,在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裡,想著美蓮的豐滿和妖嬈,我的體內便有一股燥熱。真不知道她今天玩什麼浪漫,非要來這裡喝咖啡。要照我的想法,直接訂房間更好,還不用擔心碰到熟人。
B。諾基亞手機和我的妻
美蓮還沒有到。
坐在斜對面的那對男女卻開始吵架。一開始還很克制,後來女的先沉不住氣,聲音漸漸地高了起來,有那麼幾句話便鑽進我耳朵里:「我還不如一個半老徐娘?!……還是有夫之婦,你就那麼賤,非要湊上去做人家見不得光的情夫?」
吵至激烈處,女人一把抓起男人擱在檯面上的手機往地上狠命一摜:「我讓你和她卿卿我我!」手機落到鋪著磁磚的地板上,連續翻了幾個跟斗然後就滑行到我腳下。也是閑極無聊,我居然充好人俯下身子去替他撿起手機。
是諾基亞,有藍色熒光的那種,曾經風靡一時,但就現在來說,已經很落伍了,居然還有人在用這種——不過路藍也喜歡這款機子,她說她喜歡這藍屏。
真是白天不能念叨人、晚上不能念叨鬼,我只不過在心裡想了一下路藍,就真看到了路藍!不過,不是真人,是在相片上!那個落在我腳下的諾基亞手機的背面有一張大頭貼,一對男女在鏡頭前側著臉嘟起嘴唇像接吻魚一樣親嘴!而那個女的,正是我的妻!
我呆住了,保持著一個俯身的姿勢,傻傻地將別人的手機緊握在手裡。有人在我身邊說「謝謝」並向我伸出手,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要討回他的手機。
抬起頭,我用一種憤怒的眼神看著眼前這個長頭髮的男人。我拚命壓制,才阻止了自己向他揮出拳頭的衝動。他自然不知道我心中的想法,也無心觀察我莫名的敵意,只是從我手中拿走手機。
也在此時,我的「曖昧」出現在我的面前,嗲著聲音說:「親愛的,我來了!」
是暴怒,我一改斯文,粗聲罵了句:「你以為你是什麼貞節烈女!也來裝清高!」抓起車匙拂袖而去。
我給路藍打電話:「你幾點下班?我來接你,一起吃晚飯?」
她遲疑了一下:「今天?估計不行呢!我在趕這個季度的報表,可能沒那麼早回家……你自己在外頭吃點……」不等她說完,我就掛了電話。
C。一頂綠帽子從想像變成現實
那張大頭貼,那一對嘟著嘴接吻的男女,一直在我眼前晃動。我將車停得遠遠的,然後徒步來到路藍工作的大廈對面,躲了起來。
我果然看到了那個長發男子——這並不難找,因為他懷裡那束大大的紅玫瑰讓他在人群里變得搶眼。然後,我就看到了我那冰清玉潔的妻、我那聲稱要加班的妻,抱著文件夾從大廈里走了出來。長發男子馬上迎上前去,將玫瑰遞給了她,然後兩人有說有笑地朝海鮮酒家的方向走去……
一頂綠帽子從想像變成現實,我本該暴怒,但火山來不及爆發,就被一種更深的悲哀覆蓋住,沖不出口。
怪不得,她一直力爭要出來工作……我一直以為她力求獨立,卻原來,是為了方便自己和情人約會而不被發現……
那束玫瑰,路藍並沒有帶回家,我不知道她是怎麼處理的。扔掉?情人送的花,估計她還捨不得扔掉。莫非,她和他在外頭,早有了一處固定的「根據地」?
路藍一定沒有想到,那虛偽的外衣,早在一次意外里被我洞穿。所以,她仍一如既往地裝著溫良賢淑,一如既往對我噓寒問暖。
冷眼看她,我不由得暗嘆這貌似單純的女子,城府竟是如此之深。我有外遇,多少仍心中有愧,每次和美蓮幽會回來,面對她都會有小小的不安;而她,竟似全無愧意,從頭到尾竟能滴水不漏。
她這樣隱瞞,原因不外如下:可以繼續拿著我的錢養著她的情人,等到想要名正言順雙宿雙棲時,亦可殺我個措手不及,在離婚時分我一半財產。她聰明,我亦不笨。我辛苦打下來的江山,豈容她這麼輕易掠奪?
我開始不動聲色地轉移自己名下的產業,力求將「損失」減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