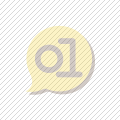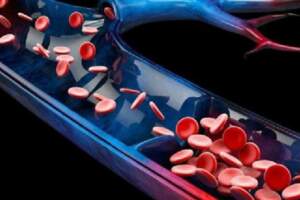房子和汽車,據說是目前中國人擁有的最大私有產權。許多人憂心忡忡,說房子才70年大限讓這種私有產權不穩當。許多一無所有的年輕人,對這種不穩定的產權也望眼欲穿,為了擁有,幾乎不惜犧牲一切。
我則提出「褲子產權說」:如果你大學畢業時的褲子日後穿不進去了,這條褲子就不再屬於你了。怎麼沒有人擔心自己對這條褲子能擁有多久呢?我提出這個問題,是覺得人們越來越只用一把尺子衡量生活:買了什麼牌子的車?買了多大的房?人家有了那個,我有了沒有?但都忘記了另外一把尺子:你為得到這個東西,究竟失去了什麼?
是更想擁有房子,還是更想擁有自己的褲子,這確實是個選擇。如今房奴、車奴充斥於世,越來越多的人為房子和汽車活著,這充分反映了這種單一價值觀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力。很多年輕人之所以能夠忍受沒完沒了的加班,心裡惦記的就是早日有車有房。若是沒有這些,自己豈不永遠當草根?
記得20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隨筆,題目叫《單純》,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文章從梭羅講起,實際上是講新婚之後我們夫妻二人的生活狀態的。在我看來,當你買任何一件自己不真正需要的東西時,就開始接受這個東西的奴役了。比如,我購買了一雙時髦的旅遊鞋,立即在家庭財政上戳了個窟窿。為了補這個窟窿,就得拿出時間去掙錢,哪怕是干自己不想乾的事情。這等於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換這雙鞋。所以,你買這雙鞋時必須想一想:這雙鞋究竟有多重要?
買雙鞋能把家庭財政戳個窟窿?確實,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狀況。當時我們只有一個人有工作,是我在中國社科院拿的200多塊錢的死工資,無房無獎金,兩人在北京很難過下去,要靠我的稿費補貼。妻子則英文、日文俱佳,當時正趕上外企大舉進軍北京,機會多多。記得有一次,一家工廠的日本專家到達,找不到翻譯,無法工作,請她去幫忙三天,一天100塊,比我的月薪還高。在那年月,這算是挺嚇人的報酬了。別人聽了也頗為艷羨:怎麼不多干點?
她從不多干。理由是:我們不會把自己的青春減價出售。我們結婚時一無所有,但都知道自己還年輕,要用青春追求新的生活,即出國留學。當時留學比現在難多了,不拿全額獎學金連簽證都拿不到。而我們決定走這條路時,英語幾乎要從頭開始學。所以,我們很明白,要儘可能把青春全部投入於自己的發展,而不是廉價拍賣。100塊一天的工作確實令人羨慕,但是,我們問了自己這麼一個問題:20年後,我們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事業,那時回首今天的青春,當是人生最為美好的時刻,難道就100塊一天給賣了?如果20年後你一小時掙1000塊的話,想想這是多麼賠本的買賣呀!所以,不賣,不賣,堅決不賣!
當然,生活要維持,必須的工作還是要乾的。但是,如果我們除了食物外基本不消費,穿舊衣服,那麼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去工作的需要,把青春最大限度地留給了自己。就這樣,我們悶頭四年,妻子先被耶魯大學的博士課程錄取;缺乏英語才能的我,得以混了個家屬的資格跟去,因為在旁聽時小有表現,很快也成了那裡的學生。想想都是多虧青春沒有賤賣,留著給自己長了點本事。
到了耶魯大學後,我先是家屬,後來讀碩士課程,免學費,但無獎學金。那時她拿的全額獎學金,其實比當地的最低生活線還少幾百塊,我們兩人一起用。那時也有些校內打工的機會,一小時能掙到八九美元或十美元,我們也都在沒有辦法時干過一點,但只要能維持生活,就不會幹。道理還是那個:青春不減價拍賣。
在耶魯大學的日子,也許是一生求知生涯最珍貴的一段。多少比我們優秀得多的人都沒有這個機會,難道就一小時十美元給賣了?記得來美國頭幾年,我的衣服幾乎全是街上鄰居搬家清理舊貨時買的,比如十美分一條的牛仔褲,尺寸不對也勉強湊合著穿。有一次走在街頭,碰到一個要飯的,他衝著我伸手。我一眼就看到他拿著一桶果汁,那牌子是我捨不得買的名牌。我心裡不禁哼了一聲,當時腦子裡轉的話,要翻譯成今天的語言那一定是:「你丫也配跟我裝窮?」
如今回想起來,那時我們的生活,幾乎是能多當一天窮人,就多當一天窮人。一無所有的狀態,其實是最為富足的。當然,我們從來沒有忘了鍛煉身體,對褲子的所有權決不肯放棄,乃至有些朋友感嘆:你們可真有工夫!如今年過半百,最為慶幸的還是:青春有價,沒有賤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