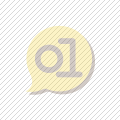哥倫比亞大學——人生新的起點
1979年9月,在田納西州生活了6年的我,已經從一個懵懂少年變成一個對未來充滿期望的青年。
懷揣著種種夢想,我飛到了紐約。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樣,這是一個集天堂和地獄於一身的城市,繁華、喧鬧、光怪陸離。來到這裡,我的第一感覺是來到了一個花花世界,眼前的一切是新鮮、匆忙、充滿活力的。
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最危險的哈萊姆區旁邊。雖然僅有一牆之隔,哥大校園卻有蒼翠山林,環境清幽,站在校園中央的日晷旁,望著四周紅磚銅頂的校舍,儼然身處世外桃源。哥大的同學多才多藝,活潑熱情,幽默聰慧,熱愛表達,他們聚在一起交流、激辯的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這所大學流淌著智慧的清泉,它將開啟我的未來之路。
哥倫比亞大學裡的哥倫比亞學院是美國最早進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學校規定學生可以進入大二再選擇專業,這給了每個學生成為通才的空間。第一年,我從必修的人文課程中收穫了讓人一生受益的知識。
傳授這些人文知識的一般都是大師級的教授,他們用開放的思維指導學生,強調學生critical thinking(批判式思考)的能力。老師上課主要就是鼓勵學生互相辯論,或是跟老師辯論。所有考試都是寫論文,而不是考背功。
我一直認為,美國的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美國教育家斯金納(BFSkinner)說:「如果我們將學過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最後剩下的東西就是教育的本質了。」他所說的正是自修之道,也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大一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美術、歷史、音樂、哲學等專業的課程,接觸了很多東西,我覺得這是找到自己興趣的機會。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哲學系的一個老教授說的話:「知道什麼是make a difference(製造不同)嗎?想像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中有你,一個世界中沒有你,讓兩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響力,這就是你一生的意義。」
這句話,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那之後,凡是我要作重要的決定,我都會想起這句「讓世界不同」的話,從而讓我的內心在作出選擇的時候更加堅定。
一般來說,除了音樂專業的院校,美國的綜合性大學是不將音樂納入必修課的,哥大卻專門設立了音樂欣賞這門必修課。此前,我從未系統地了解西方的古典音樂,但從上大學開始,西方古典音樂就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我的心。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狂熱地愛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協奏曲。
在哥大的日子,音樂老師鼓勵我們深入了解每一個作曲家的心靈故事,鼓勵我們走出課堂,去城市尋找「現場音樂」。我們經常去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小音樂廳聽音樂,也經常買便宜的學生票(大概20美元),坐在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最便宜的位置聽音樂會。實在沒錢的時候,我們就站在學校的禮堂外面聽學校交響樂隊演奏。哥大的音樂課程,使我培養了一種滋養心靈的習慣,從此之後,對音樂的愛,就一直伴隨著我。無論是工作中愁雲慘霧的日子,還是商業競爭中劍拔弩張的時刻,音樂都成為我舒緩心靈的一劑良方。
大學生活——貧窮而快樂的日子
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我剛走進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個棕發碧眼的男孩沖我微笑,「嗨,我叫拉斯(Russ),把東西放在這裡吧。」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們一起住了整整兩年半。拉斯是波蘭裔美國人,他身高178cm,骨骼寬大,他成了我在大學期間唯一的知心朋友。我們大多數時候很快樂,在昏天黑地胡說八道中度過。
我們也搞一些惡作劇,一個討厭的室友總是愛財如命,自以為是。我和拉斯趁他睡覺的時候把「kick me」(踢我)的小紙條偷偷地貼在他的屁股後面,白天他總是不明就裡地挨踢,一臉的莫名奇妙。他視財如命,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頭的零錢攤了整個屋子,然後用強力膠貼在桌上和整個地面上,他回來以後,總是大呼小叫地去撿錢。結果,才發現那些硬幣緊緊地貼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錢翹起來。我和拉斯躲在暗處,嗤嗤地憋著不發出聲音,以防笑得太大聲被他發現。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愛搞惡作劇。我經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編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車還要慢」,他也經常反擊我,「永遠找不到女朋友,見到女孩臉就比猴子屁股還紅。」
拉斯的電腦作業做得驚人得慢,一般總是拖到最後,還一塌糊塗,然後不得不找我幫忙。我已經習慣了做他編程作業的槍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業沒做,我就故意沒回宿舍,讓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實驗室補作業。當他用自己的賬號登錄時,電腦發出了警告:「今晚11點,所有機器將例行維修,無法登錄。」這意味著這傢伙必須用短短3小時趕完所有作業。對動作慢吞吞的拉斯來講,這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心理挑戰。可當他寫好程序,開始編譯的時候,電腦再次跳出對話框:「磁碟障礙,檔案已經遺失。」拉斯驚慌失措,趕緊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發生,電腦報警:「系統障礙,所有文檔全部遺失。請打開某某文檔。」他一打開這個文檔,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當了!這些障礙信息都是我騙你的。你的功課已經幫你做好了,就在你的抽屜里,回來吧!——開復。
哥大的學費加生活費大約一年1萬美元,這在1979年,對於一般的美國家庭來說,都不是一個小數目。學校一年給我2 500美元的助學金,父親給我2 500美元,貸款2 000美元,剩下的3 000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來賺。剛開始的時候,我去做家教,後來在學校的電腦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況跟我類似,他的父親從波蘭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的監獄當獄卒,收入一般,母親是家庭婦女。因此,他在學校食堂找了份廚師助理的工作,那時候,他經常從食堂帶剩下的麵包和熱狗回來,我們也經常能大吃一頓。我們的時間表也差不多。下課之後我們都去打工,半夜我編完程,他洗完碗回來,我們躺在床上閑聊,有時候時間晚了,我們倆都飢腸轆轆,冰箱裡又沒有吃的,我們就去學校附近的小店裡吃最便宜的炸雞。
有一次,我們實在太餓了,半夜兩點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國菜館,要了7盤不同的飯和面,通通吃光。結賬的時候,看到光光的盤子,服務員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下,但是什麼也找不到。「難道你們真的把這些都吃光啦?」服務員問。我們點點頭。「天啊,你們要不要叫救護車?」服務員驚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沒有錢買機票回家過聖誕節,就都留在學校里尋找打工的機會。有一天,他從學校食堂搬回來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們計劃做20個蛋糕,天天當飯吃,省出假期的飯錢。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沒辦法用普通的攪拌器來攪,我們只好倒進一個大桶里,每人拿一個棍子使勁攪。做好了,我們開始每天吃同樣的乳酪蛋糕,吃到最後,已經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這個詞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後,他突然對我說:「開復,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發霉了!」那天,我們倆坐地鐵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粵菜館,叫了6道菜來慶祝蛋糕發霉。
「做蛋糕」這個詞,後來成了只有我們才能聽懂的暗語,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歡做蛋糕的習慣保留了下來。每年聖誕節,他都要寄給我一個他親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聖誕節時他從德國寄出,等我收到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到春節了,我們全家誰都不敢吃這個蛋糕。因此,我發郵件給拉斯,感謝他從德國傳來的祝福,但是讓他不要再寄蛋糕給我了。可拉斯回信說,「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調回微軟在西雅圖的總部工作。那一年,由於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記了告訴拉斯,結果,拉斯又寄了個蛋糕到我原來的地址,結果,郵政系統查無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裡。拉斯接到蛋糕十分驚訝,他發了封郵件給我說,「你知道嗎,我一直以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種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當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聖誕節寄給你的蛋糕時,我在想,我終於有機會試試這種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開復,我把那個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還活著。」
我對著電腦一陣狂笑。年輕時一起經歷的青春歲月,是那樣的快樂和美好。人們離開大學,有著各自的生活軌跡,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時,現今一切的快樂似乎都無法取代當時那種單純的快樂。因為,我們當時是那麼的年輕、無畏、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