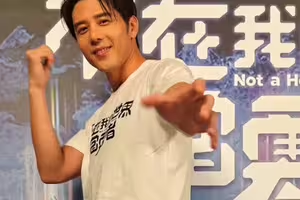1902年,在巴黎的舞台上,一位「蝴蝶仙子」翩翩飛來。她頭戴藍色花飾,身披輕盈的藍色翅膀,起舞翩躚,身姿曼妙,舞步優雅自信而又活潑俏皮。她的東方少女面孔,充滿青春的氣息,讓在場的巴黎觀眾驚豔無比。這場舞台劇《玫瑰與蝴蝶》讓西方人一下子記住了這位「蝴蝶仙子」的名字——裕容齡。她被巴黎觀眾譽為東方的「蝴蝶舞後」。
作為清末傑出的女舞蹈家,這位被光緒帝戲稱為「小淘氣」的奇女子,彷彿一隻飄忽的藍蝴蝶,穿越歷史時空而來。
晚清、民國一幕幕大戲鏗鏘上場。在硝煙紛亂的時代背景下,她猶自自由自在,沉浸在自己的中西舞蹈世界中。時光如光影變幻,怎奈何,在中共的末場大戲中,她的命運陡然發生了變化……
留洋生涯
裕容齡出生於1883年(清光緒九年),父親裕庚是清朝末年的外交大臣,漢軍正白旗人,家族本姓徐,以隨名姓的方式稱裕容齡。裕家五個孩子,三兒二女,姐姐叫德齡,她是家裡最小,也是向來最淘氣的那個。
出生貴族的她,自幼受傳統禮樂教化。融入不同民族特色的清朝宮廷樂舞給了她最初的舞蹈啟蒙和薰陶,童年時她便表現出對舞蹈的敏感和天賦。
1895年,父親裕庚出任清廷駐日本公使,全家隨行。12歲的容齡在日本舞師的指導下學習日本傳統舞蹈,以及流傳在日本的中國雅樂舞蹈,還學習了外交禮儀、美術插花和音樂。
1899年,裕庚任駐法公使。16歲的容齡與家人、隨員、僕人一行50多人又遠渡重洋,來到當時歐洲文化藝術中心——法國巴黎。容齡和姐姐德齡在巴黎讀女子學校,開始接受歐洲的文化、戲劇、音樂、舞蹈的薰陶,並經常隨父母參加各種外交活動,出席宴會和舞會。
西方的芭蕾舞藝術讓她深深著迷。她在法國國立歌劇院接受了正規的芭蕾舞訓練,後來,又進入巴黎音樂舞蹈院繼續深造,成為中國近代接觸學習西方舞蹈的第一人,也是日後第一個將外國足尖舞帶到中國的先驅者。
裕容齡的《蝴蝶舞》劇照。
1902年,19歲的裕容齡在巴黎公開演出《玫瑰與蝴蝶》、《希臘舞》、《奧菲利亞》、《水仙女》、《西班牙舞》等舞台劇。她的舞蹈才華,獲得巴黎觀眾的好評。
這一年,在巴黎郊區的森林咖啡館,裕庚全家與到訪巴黎的貝子載振(慶王長子)一起用餐。少女裕容齡穿著洋裝長裙,落落大方地站在陽光和煦的大落地窗前,與家人賓客一起合影。
她的美是光豔照人的。成長在極具中國傳統和西洋革新之風的家庭裡,她活潑大膽、果敢自信,而又舉止有儀、雍容典雅。那定格的一幕,猶如驚鴻一瞥。
御前女官
1903年初,裕庚任滿歸國,被授三品卿,留京養病。容齡、德齡姐妹倆隨後被慈禧太後召入宮中,擔任她的御前女官與翻譯,接待外國使宮夫人。這對留過洋的姐妹花,給宮廷裡帶來了清新的氣息。
容齡乖巧通達的社交能力、廣納博採的舞蹈才華與活潑開朗的性格稟賦,讓年近古稀的太後很喜愛她。對她偶爾在宮頑皮犯規,太後和皇上也總是很寬容。慈禧破格賜其封號為「山壽郡主」。從此,她開始了作為宮廷舞蹈家的生涯。
她從中國民間舞蹈和劇曲藝術中汲取豐厚的營養,創作表演了具有傳統文化底蘊的《劍舞》、《扇子舞》、《菩薩舞》、《荷花仙子舞》、《如意舞》等宮廷舞蹈作品。此外,容齡也表演自己學過的西方舞蹈,如《西班牙舞》和《希臘舞》等,這些新穎的舞蹈也受到慈禧太後和宮廷人員的讚賞。
裕容齡表演《希臘舞》。
1905年3月,父親裕庚因病到上海就醫,姐妹倆以盡孝為由,卸任出宮,趕赴上海,離開了已是多事之秋的紫禁城。不久,裕庚亡故。
幕落幕起
三年後,慈禧太後病逝。在她死的前一天,光緒帝也駕崩了。慈禧太後死後四年,大清帝國覆滅,中華民國成立。
隨著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制國家的成立,1912年,29歲的裕容齡也找到了人生的伴侶,與前清御前馬官唐寶潮喜結良緣。唐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唐紹儀的侄子,與她一樣有過留法經歷。
北洋政府時期,裕容齡任女禮官,熱心公益,參加義演,賑災籌款。夫婦倆在北京的社交界頗為活躍。
1915年,已與美國人結婚的姐姐德齡,隨夫一同赴美。姐姐德齡用英文創作的《清宮二年記》、《瀛台泣血記》、《御香縹緲錄》等作品,後被翻譯成中文,流傳到國內來,一時成為國內市民讀者關注的熱點。裕容齡在30年代用英文發表了歷史小說《香妃》,也是珍貴的文化史料。
裕容齡當年照。
即使人到中年,熱愛舞蹈的裕容齡也沒有間斷舞蹈練習。43歲時,裕容齡曾表演具有中國傳統韻味的劍舞,其身姿依舊如少女般窈窕,舞姿柔中帶剛,神采飛揚。裕容齡的這段膠片影像殘片,是由美國攝影師1926年攝錄的,倖存至今。
鼙鼓聲疾
在內戰的硝煙散盡後,1949年,沉重的歷史大幕再次開啟,這一回演到了中共竊國,橫行為主。
裕容齡的命運從這時開始,急轉直下。她和丈夫一直居住的私人府邸,很快被共產黨強行充公,闊敞的三套大四合院全部分給機關或老幹部使用。
夫婦倆被趕到附近的小四合院裡居住,只請得起一個保姆照顧粗活。紫檀木雕刻嵌鑲的大鏡子帶不了也就罷了,當年的戲裝和舞服,她倒是很仔細地裝進一個特大木箱中,隨身帶了出來。這些命根子似的寶貝已經跟了她半個世紀了。
在那樣一個「政治進步」的時代,她的傳統守舊和洋派作風愈發與潮流格格不入。古稀之年的她皮膚依舊白皙,梳著一絲不亂的髮型,眼睛明亮有神,臉上不顯皺紋,薄施了脂粉,塗上了口紅,穿著得體的黑絲絨中式上裝,顯得雍容華貴;雪白纖細的手指上,戴著一隻碧綠的翡翠戒指,高貴動人。對於法國菜和法式西點,她依舊固執地喜歡,疼愛她的丈夫就親手為她打點。
在當時萬物凋零的日常生活中,她的美,是絕無僅有的。不知是她離這個時代越走越遠了,還是時代離她越走越遠了。總之,在千人一面的灰藍色調中,她總是最招眼的,無論她怎樣低調警覺,都不能使自己沒入單調,溶於背景。
她骨子裡流露出的高雅風度,言談舉止中的溫婉從容,行事作風的不擅矯飾,眼神裡的堅韌自信,連步伐都能帶出的旋律感,乍一見面,總是讓人眼前一亮。那時的她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平時經常出入西方和東歐各國的大使館,教授俄文、法文、義大利文和英文,也教鋼琴和舞蹈。
晚年的裕容齡。
不過,一般人是不敢靠近她的,人們像避災一樣躲著她,生怕和她沾上邊倒了楣。實在是因為她的社會背景太複雜,「她是一個多麼複雜的人!」
老年的裕容齡,早已知「世事炎涼」。她對那些趨炎附勢、諂上驕下之徒也不看在眼裡。她成了共產黨幹部們的眼中釘。
於是,她把小獨院兩扇已退色的朱門閉緊,關上門來過自己的日子。她和同事漆運鈞倒是脾氣相投,兩家經常聯絡走動。
裕容齡認為自己的中文底子差,不如英文、法文水平,便常向漆老求教,學習古詩詞和古漢語。漆老年輕時曾留日,加入過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他也精通中國經史。在異常壓抑的政治氛圍下,這兩位白髮人來往切磋,作詩填詞,酬唱應和。
容齡也寫過一些回憶自己作慈禧御前女官時的懷舊短文,初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後於1957年冬集成《清宮瑣記》一書。不久,74歲的裕容齡因此書而受到批判。第二年,她的丈夫唐寶潮去世。
橫遭巨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暴伊始,裕容齡和漆老都成了 「封建餘孽」。漆老被紅衛兵抄家,一生藏書、字畫、文稿、古董均被搜羅一空,撕爛燒毀。漆老被批鬥,身上的長袍被撕扯,頭髮被剪刀胡亂剪割。
裕容齡更是飽受折磨。家裡殘存的字畫古董、家居用品被紅衛兵查抄一空,她珍藏的戲裝、舞服,包括那套蝴蝶舞服,盡數被毀。對於這些,裕容齡早已顧不得了。這位風燭殘年的孤寡老婦,被東城區一批女中學生們圍住,少女的臉個個殺氣騰騰,高亢狂暴,她被打翻在地。
對這位集「封資修」洋文化於一身的老太婆,這些十幾歲的少女們心中充滿莫名的恨,她們專打她的腿。耄耋之年的她沒有絲毫反抗能力。
83歲的裕容齡雙腿被活活打斷。連她小獨院的五間正房也再次被充公,她被轟出來,和貼身老保姆擠住在院子西北角十幾平米的低矮耳房。誰料想,昔日的郡主成了灶下婢。
從那以後,裕容齡癱在床上,臥床不起,直到1973年90歲時肺部感染病逝於北大醫院。
在終年沒有陽光的耳房內,裕容齡最後一次斜倚在床頭,從晦暗的窗口向外張望。她穿著黑色上衣,下半身蓋著被子。她的皮膚蒼白,臉頰異常瘦削,眼睛卻並未因年老而昏瞀,她的眼神是溫和的。冬日凋敝的窗口,冷冷下著雪。她似乎在張望著什麼。
她望見那隻斷了翅膀的藍蝴蝶了嗎?殘軀微微發抖,斷了的翅膀猶自掙扎著,試圖再搧動一下……
赤色大幕下,文革雖已結束,但共產主義意識還在蔓延。恨,如同一波波瘟疫,仍在中華大地流行,這樣的慘劇也將一幕幕演下去,摧毀的是中國人的道德,打掉的是中國人的骨節,焚毀的是中國人千古流傳的璀璨文化。
折斷的蝴蝶翅膀,帶給觀眾們的不僅僅是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