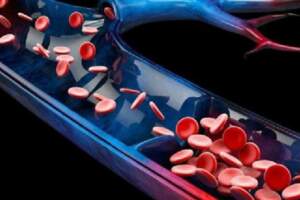街友缺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街友缺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街友缺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看著街友將自己種的菜,分送到小朋友手中,小朋友對街友說了聲簡單的:「謝謝」。過去很久的時間,可能從來沒有人跟街友說過謝謝,那一刻,芝螢看到街友眼中的欣慰。
街友的好朋友
芝螢是地方政府的公職社工師,考上高普考後,被分發到離家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政府。一開始是承辦老人保護業務,面對的是有特殊狀況的老人,例如被無家屬、被遺棄的,或是生活無法自理、行為能力有問題的,就要協助找機構安置,甚至協助老人與子女打給付扶養義務的官司。後來,她更去挑戰了從來沒有想過的:街友服務。
輔導街友種菜,是芝螢的點子。被問到為什麼想發起這個種菜計畫?她說:「在我督導街友中心的時候,正好發現中心後方有一塊閒置空地,我覺得很可惜,應該可以有些用途……,正好有一陣子流行城市農夫,我想說也許我們可以讓街友們來試試看,可以勞動,也可以妥善運用空地。」
農作收成除了供街友中心使用外,當芝螢知道鄰近街友中心的兒少照顧據點有食材不足的需求,她協助連結單位合作,由街友中心定期提供種植的農作物給鄰近社區弱勢學童食用,也因為這樣,街友們感受到自己其實有能力「給予」,而不是被動的「接受」。
 「對街友來說,她們也渴望自己可以對社會有一些回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對街友來說,她們也渴望自己可以對社會有一些回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一般人會認為街友自立是要去上職訓班、考證照,找到一份正常穩定的工作。但街友多半都是中高齡失業,學歷不高,身心狀況也不是很好,真正能上完職訓課程,考到證照的不多,而這些證照班,畢竟不是設計給街友上的,真的要街友們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成功自立,或許像芝螢一樣,根據街友的特性開發小型特色方案,並且街友中心的社工員從中陪伴、同理,讓街友透過持續勞動性質的工作是比較快的切入點。
大家都以為,街友就是會白吃白喝。但是,對街友來說,她們也渴望自己可以對社會有一些回饋。種菜,回饋給社區的孩童,這是一種比食物獲得還來得重要的心理價值的肯定。
目前各縣市政府對街友提供的服務,還是以基本生活的照顧為主,但是,談到對街友生活的重建,甚至回到工作岡位上,就比較缺乏這類的案例。雖然台北市政府曾推出「以工代賑」的方式,以社區派工的方式,讓街友在社區從事掃地清潔的工作,但這畢竟不是長期的工作,許多街友需要的是被肯定。因此,在生活重建上,需要有心靈層面、心理諮商的過程,許多街友之所以變成街友,其實是因為有精神障礙的問題。
對於一般人來說,即使想要跟街友攀談,也不知從何聊起,有些人則刻板印象認為:街友都語無倫次。於是,街友可能從一開始的無家者,逐漸遠離人群,變成城市中陌生的存在。
芝螢把自己當成中間的訊息傳遞者,透過訪談,去理解每個街友背後的故事。她說,有些街友過去曾是老闆,因為幫朋友擔保而一洗如貧;有些則是有親友可以接濟的,但是卻因為否定自己,而逃避跟親人接觸。反而,跟信任的社工談論自己的生活近況,成為街友一種寄託。
 要讓街友們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成功自立,能根據街友的特性開發小型特色方案,並且街友中心的社工員從中陪伴、同理,讓街友透過持續勞動性質的工作是比較快的切入點。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要讓街友們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成功自立,能根據街友的特性開發小型特色方案,並且街友中心的社工員從中陪伴、同理,讓街友透過持續勞動性質的工作是比較快的切入點。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無所不包的社工師
只要一旦變成了街友,就會失去社會支持。這時候,社工的角色就很重要。
曾經在台北市擔任過五年公職社工師的游旻寧說。
游旻寧大學畢業後,曾短暫在偏鄉鄉公所服務,而後投入社工工作。她說,
公職社工師承辦的案件量大,而每個案件最初接到時,都要進行一兩次的家訪。家庭訪視通常由社工師一個人進行,有一定的風險存在。相對來說,獨居老人的個案是單純的,多數老人有低收入戶資格,社工要做的是不時去關心生活起居,偶爾要協助送醫、送餐或是打扶養訴訟等等,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危險性。
 家庭訪視通常由社工師一個人進行,有一定的風險存在。相對來說,獨居老人的個案是單純的,社工要做的是不時去關心生活起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家庭訪視通常由社工師一個人進行,有一定的風險存在。相對來說,獨居老人的個案是單純的,社工要做的是不時去關心生活起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不過,還是會有遇到狀況的時候。旻寧說,有一次,到一個長期陪伴的老人家中,突然發現長者倒在地上,似乎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但是身為社工師的她,這時候仍然必須鼓起勇氣幫老人家進行脈搏測量、心肺復甦術,直到專業醫護人員來接手。最後,老人家還是走了。「中間的過程有恐懼,但同時也有很多的不捨」,旻寧說。
面對精神障礙的個案,複雜度及風險性就會提高。因為社工畢竟不是心理諮商師,很難去做專業判斷,更棘手的是,有些個案是抗拒心理輔導的,即使要轉介也無從著手。在這樣的情況下,社工就會變成一個抒發的窗口,一方面感到被信任的成就感,但另一方面,也得留意個案是否有不正常的行為出現。
「社工的工作,真的很五花八門」,特別是對於一些經濟弱勢的家庭,還要協助她們管理帳務。有的時候,這些家庭對於金錢的概念是「來得快去得快」,一拿到錢,還沒去處理欠繳的房租,就先帶小孩去打牙祭了。這時候,社工還得去協助個案跟房東之間的欠租協調。「但有時候社福補助款真的來得太慢,我就會先拿自己的錢給個案,最多曾經先墊了10萬元」。
 「社工的工作,真的很五花八門」,特別是對於一些經濟弱勢的家庭,還要協助她們管理帳務。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社工的工作,真的很五花八門」,特別是對於一些經濟弱勢的家庭,還要協助她們管理帳務。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從服務中得到的生命體會
不過,各式各樣的社會邊緣人,也成為社工人生中不同的生命體驗。
芝螢跟旻寧都提到,從事街友業務時可以看到街友共享的系統,街友們會好康道相報,哪裡有好吃的,大家都會知道;有時候有人接到臨時工,比如說陣頭、或是工地活,就會介紹其她人一起去。大家都知道彼此生活不好過,因此形成一種互相扶持的連結。
芝螢跟旻寧有個共同點,都透過創新的方式,為社會弱勢的族群做一點什麼。芝螢自己創辦一個粉絲頁「打狗街頭二三四」,紀錄著街友的故事,有許多人因為看到她的粉絲頁,因而能開始同理街友的情況。芝螢的文章中常傳達出一種訊息:原本缺乏信心的街友,透過一些小小的成就感,逐漸找回信心的喜悅。
為了讓大家體驗街友的生活,她輔導的社福民間團體還設計了「漂泊33-街友生活體驗營」,讓青年在33個小時中,到街友中心跟街友聊天、一起工作、一起露宿街頭,體驗人生中許多「不得已」,另外,芝螢還自製「露宿者生存地圖」放在粉絲專頁上,用簡單輕鬆的讓大眾知道街友有那些生存技巧,哪個地方可以不會淋到雨,可以好好睡一覺的,或者是那一家的愛心餐比較好吃。
芝螢說,她很感恩有這個機會讓她歷練學習,也讓她可以認識這些街頭的朋友。她覺得這些街頭朋友也是一種另類的「導師」,在與他們互動的過程中,教導她許多人生大大小小的道理,也因此,她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什麼樣的方案對於街友可以有更確切的協助。
在接受採訪的此刻,旻寧已離開公職社工的職位,現在從事弱勢族群教育推廣的工作,希望在不同領域服務社會弱勢的民眾。其實,在社工師的期間,她就曾企劃導入藝術輔助治療,去協助精神障礙的個案。問到為何選擇暫時離開公職社工,她說,因為自己出現了輕微的創傷症候群,讓她只能暫時離開這個工作。
不過,她認為自己的心中,還是有一份社工魂。她回頭想,這段曾經擔任社工的經歷,讓自已對於生命有許多的體悟,現在而言,不論面對什麼樣的困境,都能夠比較豁達地看待。
社工師,這個職業賺的或許不多,但是,會從遇見的人們身上,看到很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回過頭來,會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也更認識這個社會隱而不現的那一面。
 「社工師,這個職業賺的或許不多,但是,會從遇見的人們身上,看到很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回過頭來,會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也更認識這個社會隱而不現的那一面。」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社工師,這個職業賺的或許不多,但是,會從遇見的人們身上,看到很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回過頭來,會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也更認識這個社會隱而不現的那一面。」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對社工工作環境的期待
對於社工環境的期待呢?芝螢跟旻寧兩人都同時提到,目前民間社工的待遇情況普遍不佳,社福機構的社工起薪在22,000~30,000之間,有時還被要求要回捐給機構。因此,許多社工系畢業的同學,還是會想要參加高普考,成為公職社工師。
另外,除了保護性社工有危險加給,從事社福工作或承辦業務的社工並沒有危險加給,面臨突發狀況時,也無法即時取得警政單位的協助(除非個案已經有自傷、傷人的行為出現);進行個案訪視時,也要靠自己協調尋求心理、公衛系統的支援,缺乏橫向支援的窗口連結,讓社工有時會感到心有餘力不足。
社工在社會上常常被誤認為是志工,也常被認為要有愛心而須某種程度的犧牲付出。大家都知道弱勢團體需要幫助,但是,當社工本身的工作處境也處於一種弱勢之時,誰來替社工發聲呢?因為有社工的存在,讓一些社會問題得以在擴大前先被預防,但是,當社工發出預警性的訊息時,我們的政府,聽到了嗎?
 社工在社會上常常被當作志工,被要求必須某種程度做義務的付出。大家都知道弱勢團體需要幫助,但是,當社工本身的工作處境也處於一種弱勢之時,誰來替社工發聲呢?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社工在社會上常常被當作志工,被要求必須某種程度做義務的付出。大家都知道弱勢團體需要幫助,但是,當社工本身的工作處境也處於一種弱勢之時,誰來替社工發聲呢?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社工的自我調適能力 社工面對各式各樣的民眾,有些拿不到社福補助款的民眾,會當場飆罵髒話,給 社工難堪。不過,站在公眾服務的立場,除非有暴力威脅,否則是很難請民眾離 開的,就只能忍耐、好言相勸。 這些情緒上的累積,會不會成為負擔呢?旻寧認為社工師的特質在遇到挫折時,會比一般人能夠調適。當然,社工系統也有一套團體督導的制度,會定期找外面的老師來協助社工成長。旻寧認為,她之所以能保持健康的工作心態,身邊的伙伴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