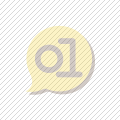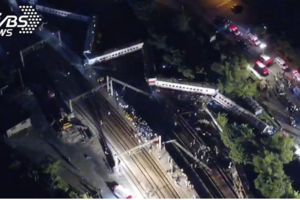一
早上,梅彩兒特意用人蔘炖了罐雞湯。丈夫胡玉堂近些日子形容憔悴,她正想方設法給他食補呢!胡玉堂在街頭文盛魁當大掌柜,管著幾十號夥計。胡玉堂有夜讀的習慣,他怕驚擾她休息,就搬到後院的書房了。每天早上,胡玉堂按時吃飯,吃完飯後就去柜上;可今天早上,胡玉堂似乎還沒起來。這不,雞湯都炖好半天了,胡玉堂還沒過來。
「珠兒,去喊老爺吃飯。」梅彩兒一邊梳妝一邊吩咐丫頭珠兒。
「是,夫人。」珠兒應聲去了。
珠兒來到後院,發現老爺的房門沒開,她愣了一下。每天這個時候,老爺早出門去商號了,怎麼現在還沒出來?珠兒就在門外喊,可屋子裡靜悄悄的。莫非,老爺睡過了頭?珠兒輕輕推開門走了進去。老爺的床上空空的,被褥收拾得乾乾淨淨,老爺去了哪兒呢?不知為什麼,珠兒突然覺得老爺的房裡陰森森的,一股冷氣躥上她的後背。珠兒一抬頭,驚得魂飛魄散——原來,老爺竟然吊在了橫樑上!
「夫人,不好了,老爺出事了!」珠兒臉色蒼白,一路哭腔地跑到了梅彩兒面前。
「這丫頭,有話慢慢說,老爺怎麼了?」梅彩兒從妝奩里取出金釵。
珠兒道:「夫人,老爺他、他上吊了!」
「珠兒,你說什麼?老爺上吊了?」梅彩兒剛準備插在頭上的金釵掉在了地上。她跑過去一看,頓時癱倒在地,號啕大哭起來。昨晚上老爺還好好的,今天早上怎麼就上吊了呢?不過,梅彩兒慌中不亂,她吩咐珠兒去找西鄰的二老爺胡玉萱。
盞茶過後,胡玉萱驚惶失措趕來了。他將胡玉堂的屍體解下,罵道:「梅彩兒,我哥為什麼上吊?定是你勾結姦夫謀害了他!」
「玉萱,你怎麼血口噴人?我和你哥夫妻多年,怎麼能謀害他呢?」梅彩兒分辯道。
胡玉萱冷冷道:「別以為你和鄭稔年勾勾搭搭的我不知道。我沒工夫在此和你理論,我這就上衙門告你去!」
胡玉萱不容分說,出門直奔衙門去了。知府張敬修正在後堂和師爺閑聊,忽聽前堂傳來擊鼓,張敬修趕緊穿上官服來到堂前。
張敬修是嘉慶十三年進士,為官清廉,不畏權貴,前年從保定府謫放到廣寧當知府。雖然到任不滿三年,廣寧已是政通人和,一派繁榮景象了,因此,張敬修深得百姓愛戴。
張敬修坐到堂上,讓人把擊鼓之人帶上堂來。隨著衙役們的堂威喊過,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被帶進來跪在堂下:「小民胡玉萱,狀告嫂子勾結姦夫謀害了家兄胡玉堂!」
「可是文盛魁的當家大掌柜胡玉堂?」三天前,張敬修還和胡玉堂在鴻寶樓喝過酒呢!
胡玉萱點頭:「正是家兄。」
胡玉堂乃一方名士,早年也曾飽讀詩書,後來奉行祖訓棄文從商,當了文盛魁的大掌柜。文盛魁是廣寧乃至關東地區屈指可數的大商號之一,是胡玉堂的先祖胡輯五和股東徐春圊共同創辦的,文盛魁能發展到今天,胡家幾代人功不可沒。
張敬修到廣寧不久,即到文盛魁拜訪過胡玉堂,兩人不久即成知交。現在聽說胡玉堂被人謀害,心下也是一愣,當即問道:「胡玉萱,你說你嫂子謀害了令兄,那姦夫是誰?」
胡玉萱道:「姦夫就是嫂子的表兄鄭稔年。當年,他曾和嫂子有過婚約,後來嫂子嫁給了家兄,兩人仍有來往。昨天晚上,我看見他從家兄家鬼鬼祟祟離開。所以,家兄的死,他難逃其咎!」
「好,隨本官前去勘查!」
於是,在師爺和捕快李子坡等人的簇擁下,張敬修起轎前往胡玉堂家。胡玉堂直挺挺躺在地上,梅彩兒正在一旁痛哭,一見張敬修進來,撲通跪下:「大人,您可要為民婦做主呀!」
張敬修讓梅彩兒起身,問胡玉堂最近有沒有什麼異常,梅彩兒想了想道:「大人,我家老爺最近似有什麼心事,可我問他,他卻閉口不說。」
梅彩兒回憶說,最近這些日子,胡玉堂的心情一天躁似一天。一天晚上,她給胡玉堂送夜宵,聽到胡玉堂在說胡話,至於是什麼內容,她沒有聽清。她只聽到話里有「鬼」、「求饒」、「寬恕」的字眼,沒想到今天早上,她叫丫頭去喊他吃飯,卻發現他弔死了。
張敬修聽了,便去看胡玉堂的屍身。他發現,胡玉堂脖子上的勒痕並不明顯,卻依舊清晰可辨。
梅彩兒是胡玉堂娶的第三房夫人,頭房妻子柳月仙產後不久去世,剛生不久的兒子也在觀燈時走丟了;二房夫人生下兒子殿雲後,也患癆病死了。張敬修對胡玉堂的家庭很了解。梅彩兒比胡玉堂小十三歲,正值如花的年紀,而胡玉堂已經五十過頭,難免琴瑟不和;難道,真是梅彩兒勾結情夫將其謀殺不成?
張敬修發現,房梁很高,上面還有尚未解下的繩索,胡玉堂身材矮小,地上的板凳尚不及膝,從繩索到板凳的距離來判斷,胡玉堂不可能踩著這個板凳懸到樑上;再說,勒痕也並不明顯……看來,胡玉堂應是死後被人懸到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