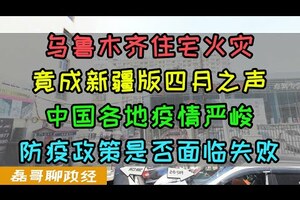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夏天,饒平如的父親來了一封信,希望他借著假期回家訂親。「父親即帶我前往臨川周家嶺3號毛思翔伯父家……我們兩家是世交。走至第三進廳堂時,我忽見左面正房窗門正開著,有個年約二十面容嬌好的女子正在攬鏡自照,塗抹口紅—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美棠的印象。」
「覺得美嗎?」中國主持人柴靜問。
「那時覺得女孩子都是好看的。」老先生老實說。
兩個人也沒講什麼話,父親走過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指上,人生大事就這麼定了。兩個青年都覺得好笑,笑之餘,去她房間坐,妹妹們繞床玩,美棠拿張報紙捲筒,唱歌,還拿相冊給他看。
他覺得她大概是喜歡自己的,從相冊中抽了幾張帶走。
回軍營路上,他穿軍裝站在船頭,看滾滾長江上波光,覺得自己的命從此輕慢不得,因為命裡多了一個人
他最喜歡美棠的一張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鮮明的臉,捲髮尖臉細彎眉,放大貼在軍營牆上,還把照片分贈給戰友—我簡直不能明白男生這種心理,問他,他承認「還是有幾分得意的」。之前鄰居有十四五歲的少女常來,有日,看到照片,問:「你女朋友?」臉色一黯,後來再沒來過。
內戰之後開始,他不想打,請假回家成婚。
冬天正要邁入它最冷的日子,那麼離春天也不再遠了
一九五八年,他被勞動教養。沒人告訴他原委,也沒有手續,他被直接從單位帶走。
單位找他妻子:「這個人你要畫清界線。」
關口上,美棠說的話透出一股脆利勁兒:「他要是搞什麼婚外情,我就馬上跟他離婚,但是我現在看他第一不是漢奸賣國賊,第二不是貪污腐敗,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一個人,我怎麼能跟他離婚。」
饒平如去了安徽一個廠子勞動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每年只能回來一次,二十二年,一直如此。
他幹的活是獨輪車運土修壩。兩三百斤的土,拉車還可以兩個人一起,輕鬆些,但他選推車,為的是一個人自由,可以把英語單字放在衣服裡,一邊默背,知道沒什麼用,只是不願意生命都消磨過去了。
家計陡轉直下。動盪的年代,五個孩子正要度過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長大成人、讀書學藝、上山下鄉、工作戀愛。岳母日漸年高,所謂母老家貧子幼,家中無一事不是美棠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邊太多家庭妻離子散,親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們從沒有起過一絲放棄的念頭,」饒平如說。
美棠自己為了補貼家用,卻常找些臨時工的活來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館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碼五十斤重,她也從此落下腰傷。
兩地相隔,饒平如和美棠從未中斷過書信聯繫,孩子們稍大些後,也都爸爸保持通信。
饒平如回憶,「有一日晚飯後,我正有一封信要寄回去,摸摸口袋尚有一把錢幣,懶得去數,便到櫃檯前問營業員買一張八分錢的郵票。付錢時候我掏掏口袋:一分、兩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沒有了!還差一分錢,營業員收回郵票,我也只好收回硬幣,帶著寄不出去的家書回去了。」
柴靜問:「中間二十年,相隔兩地,沒有怕過感情上出問題嗎?」
「想都沒想過。那首歌裡唱的,白石為憑,日月為證,我心照相許,今後天涯願長相依,愛心永不移。這個詩說得很好,天涯,這個愛心是永遠不能夠移的。」
這是美棠最喜歡的《魂斷藍橋》裡的歌詞。青年時代沒有那麼重的憂煩時,家中如有客,她讓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現在她不在了,他九十歲才學彈鋼琴,為的就是常常彈這支曲子,是一個緬懷。
一九九二年,美棠腎病加重,饒平如當時還在政協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心照顧妻子。從那以後,他都是五點起床,給她梳頭、洗臉、燒飯、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還要打胰島素、做記錄。他不放心別人幫。
一次訪談中,主持人柴靜問到:「您心裡有煩躁的時候嗎?」饒平如則說,「沒有,沒有,這個一點都沒有,這個是我的希望。」
後來,美棠在病痛中漸漸不再配合,不時動手拔身上的管子。她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畫畫勸她不要拉管子,但畫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著她,但畢竟歲數大了,不能每天如此,還是只能綁住她的手。
「她叫『別綁我』,我聽到很難過,怎麼辦⋯⋯很痛苦。」
美棠犯糊塗越來越嚴重,有一天稱丈夫將自己的孫女藏了起來,不讓她見。饒老先生怎麼說她都不信,他已經八十多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著他哭,像看不見一樣。
他說:「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楊絳寫的這句話,『我們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們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饒先生的孫女說奶奶從那以後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當她是說胡話的時候,只有爺爺還一直拿她的話當真。她從來就是挑剔品質的人,她要什麼,爺爺還是會騎很遠的車去買哪個牌子的糕點哪個店鋪的熟食。等他買了回來,她早就忘記自己說過什麼,也不會想要吃了。勸不聽的。奶奶說她那件並不存在的黑底紅花的衣裳到哪裡去了,爺爺會荒謬地說要去找裁縫做一件」。
饒平如87歲時,美棠去世,因為想念,老先生開始學畫,一筆一畫記錄下與美棠的一切,四年時間平如手繪了18本畫冊,講述他與妻子相濡以沫的六十年光陰故事。命運無奈,他們在長久分離22年後才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美棠身患重病且漸漸失去記憶,她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饒平如說:「人人都要經過這一番風雨,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白居易寫『相思始覺海非深』,到了現在我才知道,海並不深,懷念一個人比海還要深。」
主持人柴靜曾在節目中問他:「您已經90歲了。難道這麼長時間,沒有把這個東西磨平了,磨淡了?」
老爺爺回答:「磨平?怎麼講能磨得平呢?愛這個世界是很久的,這個是永遠的事情。」
原來一個人可以把愛過的人記得那麼牢,那麼細。
一生短嗎?對於習慣速食愛情的人們來說,一生太過漫長,怎麼能只愛一個人?一生長嗎?對於饒平如和毛美棠來說,一生實在短暫,還沒有愛夠一個人,一生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