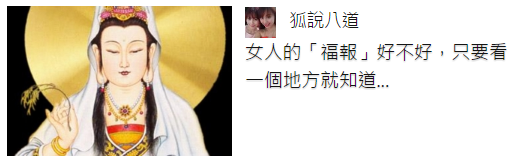我想有錢,但不是想發財,我得為了微微——木木的女兒賺錢,她倒好,三十樓一蹦噠,把三個月的女兒留給了我,也不叫留給我,是她已經沒有任何親人了。木木是孤兒,小的時候父母就不在了,十五歲時爺爺奶奶也過世了,在埋了兩老後就帶著幾件衣服去了深圳,十五歲了,可以養活自己了。
我雖說大學畢業,可尼瑪浪費的不止時間,還有金錢,到頭來還不如木木,我來深圳找她時,她做到一家酒店經理了,我只能在身上錢快用盡的時候選擇了一家小公司做文員,做過的都知道,能做文員條件兩種,一是漂亮無學歷的,一是有學歷不漂亮的。
木木的故事俗套,香港老闆想兒子,但木木生了女兒,香港老闆就消失了。木木想不開,從酒店三十樓跳下,樓頂放著女兒。
當我從酒店人員手中接過微微時,我不知道怎麼抱這個毛東西。帶回租房時,在狹小的空間裡她哭得肝腸寸斷,她是在難過她母親的離去嗎?我呆呆地坐在旁邊,腦子一片空白。鄰居郭姐可能是被吵得實在受不了了,大聲拍門才將我驚醒。
“你!哪來的?誰的?你的?拐的?撿的?”
“我,我朋友的。我們一個村的。”
郭姐一把抱起孩子,“崽子哭得真狠,餓了吧,啥時候吃的?吃奶粉還是母乳?她媽呢?”
“她媽跳樓了。”
“啊?”
我這才知道這個小東西要吃奶,要換尿不濕。一陣慌亂外出採購安頓,小東西被郭姐哄睡了。
“郭姐,你怎麼會帶小孩?”
“姐離異,有娃的,判給他爸了。”燈光昏暗,看不清郭姐表情。
臨走郭姐列了清單,要我買的東西,我已累到不想動彈。我做了一個夢,夢里木木有話對我說,我聽不清,我很使勁地聽,豎著耳朵聽,聽啊聽,聽到了微微嚎啕大哭的聲音,郭姐在外拍著門:“丁月,娃要喝奶啦!”
天!這我才剛合眼啊!
天亮了,我收拾起床上班,對,上班,準備出門發現滴溜溜的眼睛看著我,靠,這有一祖宗,我上班了,她怎麼辦?放床上?關房間裡?尿了怎麼辦?餓了怎麼辦?我好想說,妞,你自己管自己吧,我要上班了,我一月掙三千大洋,但昨晚你已花了一千多個了。
我到公司時,所有人的目光都詫異地望著我,有見帶貓狗上班的,沒見帶娃上班的,微微還好,吃飽喝足不吵不鬧,我大方地回應看她的人,微微,是的,我在來的路上給取的。老闆來的時候臉黑得像包公,老遠就指我,叫我上辦公室。我的心像鼓一樣敲著。
我把孩子交給郭姐,一進辦公室就給他跪下了,嚇得老闆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聽完我要多苦有多苦,淚流滿面的描述,一個大男人眼也紅了。
帶娃肯定影響工作,扣工資五百,一個月後如不能解決,帶娃一起走人。
公司小就是好,老闆說了算。
郭姐午餐幫我打上來在辦公室一起吃的,她問我:“你想怎麼樣?什麼時候送福利院?”
“送福利院?為什麼?”
“怎麼?你想自己帶?”
郭姐看了我一眼,“你,未婚,沒養過孩子,還,沒錢,你怎麼帶?你想過嗎?孩子要吃奶粉,要穿衣服,要買尿不濕,生病要看醫生,你那點工資在深圳想養娃?比天方夜譚還天方夜譚。
我知道。我才工作不到一年,吃飯要錢,租房要錢,原本想房子到期住宿舍的,可現在……
“我先帶著,過些時候送回老家吧。她沒一個親人了。”我沉默。我不知道我媽知道會怎樣。
下班回家,看著微微躺在床上,眼睛滴溜溜地亂轉,她現在還好無邪,已不知她生母已離去,電話響了,酒店的人說木木有些東西要我去領回來,還有木木的骨灰。
我想回家,可家裡還有一個弟弟等我這點薪水,母親已做不動太多農活,父親早前在開山時出意外走了,我的大學一大半是木木支援的,她說要我完成她的夢想,她說我長得醜還不讀點書以後沒男人要的,她說當年把我從崖邊拉上來時,就當我是她的妹妹了,她永遠罩著我,她說我們是大山的女兒,在哪都能活,可是木木你……
我知道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沒錢萬萬不能的,我要養這個孩子,無論何種方式,都離不開錢,所以我要賺錢,我要有錢!
我決定去擺夜市賣湯圓,下班讓郭姐幫我看娃,把房東曾經的三輪車攤子收拾了,穿過兩條街,在一個大工廠的門口支起了攤,湯圓料是早早在菜場買的,第一天賣了十多碗,連本帶利賺了四十幾塊錢,嗯,奶粉錢有了。第三天下雨,第四天去晚了,位置被別人佔了,也是賣湯圓。第五天剛擺上被幾個男人掀了,我身上都是湯圓粉。
這個不行,我換別的,去小商品市場批發了一些小飾品,賣了三天,就賣了十幾塊錢,這個簡單,用塊布擺地上,搞個充電小檯燈照著,如果有人趕我撈起就跑。收攤回家,郭姐看我累得不想動,直接帶微微睡覺了。
我想這太慢了,還是賣湯圓賺得多些,可是被人趕的問題我解決不了,我鬥不過那些人。
我在原地他們趕,那我就走著賣,我把攤車送去修修,開始邊穿工業園區邊賣湯圓,郭姐看我每天回家坐在那將錢一張張地捋平,一副財奴的樣子笑說:“你還不如樓下小髮廊的,人家一晚上比你總數還要多。”
我回道:“姐,我倒是想去,可我沒漂亮臉蛋不說,該像個女人的地方我一個沒有,我怕我去了人家以為我是嫖客。”
郭姐笑得險些摔倒,收了笑:“要不我找人幫你養這孩子吧?”
我看著郭姐:“姐,孩子我不會送人的。”郭姐怔怔地看著我,也許是我的嚴肅讓她尷尬了,她一言不發地回去了。
日子很快,馬上快一個月了,我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我要回家一趟。我知道我在公司幹不下去了,晚上太累,白天做事老犯錯,不說老闆,我自己也呆不下去了。還有我要送微微回家。
當我和微微出現在村口時,母親面無表情,幫我抱微微回了家。孩子在炕上自娛自樂,母親臉上才有了點柔和:孩子你送福利院去吧,我們養不活,弟弟還在讀書,指望著你打工掙錢供他。
“媽,錢我掙,但孩子我不會送福利院的,我的命是木木給的,我要償還的。”知我倔脾氣的母親繃著臉的坐在了炕頭。“姑娘,你還沒嫁人,你帶著個娃是個什麼事?”
“我知道,我可以今生不嫁。”
“你!我老了,可看不了孩子了!”母親甩手出去了,夜半醒來看見她坐在炕邊發呆。
我決定還是帶微微出門,臨行前我帶微微去了木木的墳頭,什麼也沒說,但孩子哭了,不知木木聽見沒?
回到郭姐那,郭姐接過微微,我告訴郭姐我要帶著微微一起去賣湯圓,我把三輪車改下,掛個嬰兒車就行了。
那天,天涼風大,沒什麼人出廠門,正想早點回去,有個人站在我攤前,點了一碗湯圓,看我下湯圓的功夫,跟我聊天:你一個人帶孩子呀?你老公呢?我笑了笑:我沒老公。
“你是單親媽媽?”
“算不上。”
那人的聲音很好聽,讓人有種麻麻的感覺,我記得他連著有十天吃我的湯圓了。
就那麼一下,他從我手中接過湯圓的時候,他的手有點熱,那種熱度傳到了我的胸口。他笑了笑站在攤邊看著我:“你要回家了吧?”
“嗯。”
“要不我送你?”
“啊?不用了,真的。”
我努力使離去的背影看起來不那麼吃力,眼淚卻止不住地流下來。轉彎的時候偷偷轉過頭看去,只看到他進廠門的背影。
入深秋了,微微咳了一天了,我一邊搓湯圓一邊看著微微,她小臉咳得通紅,餵水也不喝,我想等下收攤回去,帶去租房樓下的門診看下。正想著聽見有人要湯圓,抬頭看到他正笑瞇瞇地站在攤前。
“今天生意怎麼樣?”
“還行,也快收攤了。”
湯圓下鍋,微微咳得吐奶了,我一下把手裡的東西都丟了,抱起微微拍她的背,“她生病了?”
“嗯。”
“那趕緊去醫院呀!”
“我等下去!”
“孩子都病成這樣了,還等!”
他摸了下微微,從我手中抱過孩子,朝廠門值班室喊了聲:“老王,幫忙把湯圓車推進去下!”話語間已經抱著孩子往路口跑了,我連忙跟上。
醫生說萬幸來得早點,如果晚了怕是要燒成肺炎了。掛了點滴,小臉也不紅了,已經安靜地睡了。
“這是誰的孩子呀?”我這才想起是他帶我來醫院的。
“錢我明天給你,攤子我明天去推回,今天謝謝你了,很晚了廠門要關了。”我不想看他,他沒做聲,好半天我一回頭,他還站在旁邊,見我發現他,他笑了笑:“我叫李祥,今年二十七,在俊得電子廠做部門經理,你的事多少知道點,如果可以,我想幫你。”
我笑了:“幫我?呵呵,怎麼幫?養我們倆麼?”
“可以。”他回答的速度讓我覺得臉上燙了起來。我不敢看他的眼。
往後的日子,他每天下班都來攤上幫我,哪怕我轉了幾個街角,離俊得電子廠遠遠的,他還是能找到我,來了也不說什麼,到了就幫忙,實在幫不上就帶微微。微微快一歲了,開始呀呀學語了,他逗她:“叫叔叔,叫叔叔。”看著他倆一個逗一個笑,如同一幅畫,就著路燈的光在我心裡慢慢長成了一朵花。
臨年關的一個晚上,我叫住李祥:“李祥謝謝你,我們,真的不可能,我家裡除了我媽,還有一個正在讀中學的弟弟,我爸早死了,山里沒有男人,什麼錢都掙不出來,我賣湯圓除了養微微,還要供弟弟讀書,我無法擁有平常人擁有的,你不一樣,你年輕有為,事業有成,可以找個相當的女生談戀愛,我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拖累,你要是找了我,最起碼十年不能翻身。”
他笑著看我:“很晚了,收攤吧。”
送我回家的路上,看他賣力地騎著三輪車,我抱著微微跟著,到租房樓下,他像往常一樣,幫我把車停好就走,我拉住他:“微微該叫我姐姐,她是一個比我大一歲的,我該喊小姨的人的女兒。”
是的,按輩分我得叫木木一聲小姨,村子里大都沾親帶故的。
但木木從來不讓,只讓我叫姐。
晚上在租房裡我抱著微微淚流滿面,奶粉不敢吃差的,衣服都是房東送的,還有郭姐買的,家裡每月都要寄錢。
誰找我誰倒大霉的,我沒告訴李祥,他母親來找過我,一個乾淨體面的老太太,沒有哭嚎辱罵,只在攤邊看我賣湯圓,做湯圓,她淡淡地對我說:“妹子,你人好手也靈巧,但負擔太重了,於誰都是一種拖累。”
當我知道她是李祥母親時,心底那顆小花一下子連根折斷了。
離開深圳來中山幾個月了,這工廠多,但廠子都大,一個廠門賣了到下一個廠門要騎很遠,年後微微會走了,怕她瞎跑,我只有拴個繩子,一頭在她身上,一頭在我腰上。
看著那些廠區寫字樓出來的姑娘們,心想:要是我也從這寫字樓裡走出來會是什麼樣,想歸想,湯圓還得賣,人生就是這樣,上天安排好你的位置,該擔怎樣的責任就該怎樣做。
那天,正擺攤準備做湯圓,微微突然朝一個方向歡快地張著小手,咯咯地笑,一個人影走近了:“丁月,來碗湯圓。”
一年後,我守著小店,店子開在俊得電子廠邊,微微在店門口玩耍。
我想起有一晚我把她抱到商場門口想放下她時,她沒有哭鬧,靜靜地望著我笑。
那個笑讓我堅定了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