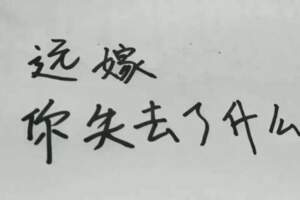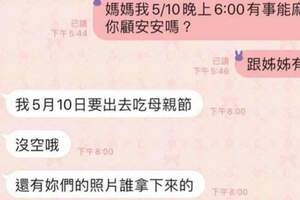她謙遜。
在美國時,她靠著自己的經濟知識買賣股票,
每有盈餘,就要買近處的房產出租。
其中兩處,尤為著名。
一處是英格麗·褒曼曾經鍾愛的臨泉別墅,
另一處則是伊麗莎白·泰勒的故居。
可她幾乎從未不多提。
她才華卓絕。
她5歲時讀中國傳統的私塾,
16歲又以優異的成績從奉天女子師範畢業。
嫁給少帥張學良之後,她在家務之外,還要抽時間去瀋陽的大學聽課。
目的是為了補足自己的知識,好幫助少帥。
後來與宋美齡結拜金蘭後,她便決定要向宋美齡學習,
學她的善良、誠實、豐富的學識以及優雅的風度。
與宋美齡相見時,張學良曾親口承認,
有時軍政大事經常與自己的妻子談論,並聽取她的意見。
她為人妻,生死不渝。
她說,“ 我生是張家的人,死是張家的鬼。 ”

在久居好萊塢山上的住宅裡,進門大廳的牆上,
掛著一張張學良戎裝的照片,她每天祈禱聖母,
保佑張學良早日獲得自由,快來與家人團聚。
她甚至表明,若是有人去看她張學良夫人,她很歡迎。
若是去看她於鳳至,她將不會面。
她的墓碑上的英文名是鳳至·張,從未加上自己的姓氏“於”字。
她便是張學良的髮妻於鳳至。

西安事變後,匆匆與少帥一別,竟是天各一方,五十年光景橫擔在夫婦之間。
她的後半生,一直在等張學良的到來,但直到1990年3月30日,
九十三歲的她長眠在洛杉磯比佛利山玫瑰公墓,這個願望依舊沒有實現。
讀於鳳至的回憶錄時,經常能看到她風華絕代時的照片。
她梳著新潮的短髮,留著柳梢似的劉海,
看起來榮華富貴集一生,卻又弱柳扶風般精幹,一雙明眸顧盼生輝。
與宋美齡義結金蘭時,她站在中間,本來纖細的她,
被宋家大姐與三妹擠得只剩一條細線了,
可那嫵媚靈動,端莊氣質,讓人看了仍舊目不轉睛。
就連從小在美人堆裡長大的愛新覺羅·溥傑
也讚嘆她美得猶如一枝雨後荷塘裡盛開的蓮。

可在讀她的文字時,彷彿那位瘦得快趕上趙飛燕,
能做掌上舞的於鳳至,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她文字洗練,鏗鏘有力,大有殺伐決斷之姿,每每說到她的丈夫張學良時,
便用他的字,漢卿,來指代,可是,讀起來全然沒有小家碧玉,
兒女情長的嬌嗔,總是給人以居於時代變幻的高台,
看遍風起雲湧,大有指點江山之風。
她談政治,描述之間,便引用“漢卿說”,甚至還有“漢卿沉痛地說”。
字裡行間,對丈夫的敬佩之情,躍然紙上。
她寫自己的事,不待解釋清楚,便急忙地轉到漢卿的名字上去了。

說來或許荒謬,我一直覺得心中有大義,
能取捨的女子,在愛情方面反而能愛得更忠誠,也更深邃。
這樣的女子的愛戀經歷不會很多,也不會跌宕起伏,
多是平淡的,艷遇與她們絕了緣,
曠世戀曲譜得也好像哪裡不對勁,悲情不如別人,幸福也比別人差了一截。
而她們有的,是全然不同於別人的無形的高貴。
於她們,大談容貌之美,是看低了。
而大捧才學技藝,又顯得俗氣。
她們身上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精神,
那是一種一般小女人終生都無法具備的韌性。

她說到自己的情敵時,既沒有一腔妒忌,更沒有使勁喊冤。
她更多的是不屑。
她知道少帥對女人十分隨便,但她從不過問。
只有兩次例外。
張學良曾想納王正廷的妹妹做二房,說她人品好,留學歸國,學識很高。
並且王正廷的人脈關係與政府要人都有淵源,張學良一再要求,她還是拒絕了。
最後張學良依從了她的建議。
而她談到,據說後來與張學良譜寫了曠世奇緣的趙四小姐時,心中更加坦然。
沒有詆毀趙四,也沒有誇讚她,只是擺事實講道理,讓旁人自己去評判。
她首先點出趙四隻是張學良眾多追求者中的一個。
父親是政府中主管經濟的要員,
她因終日在舞場流連、不肯上學,被稱為趙四小姐。
她追逐少帥,報紙上大肆報導。
她父親管教她,她不聽,
便登報脫離了父女關係,成為最熱門的新聞。

在她的口中,趙四為了自己的私心,借了與父親斷絕關係的由頭,
託人找到她,要求出任漢卿的永久秘書,服待漢卿生活。
趙四一進門就跪下,向她磕頭,保證一輩子不忘她的大恩大德,
一輩子只做漢卿的秘書,決不要任何名分。
那年,趙四小姐十四歲。
周遭一片反對之聲,至親好友都勸她,說這種好玩的小姐,
不僅沒道義可談,對自己的父母尚且如此,今後對你與少帥還不知道會如何。
她思慮再三,還是心軟了。
她拿出自己的錢給趙四買了一所房子,還告訴財務人員,給她工資從優。
後來,在少帥自由受限、長年監禁之時,
趙四小姐對少帥照顧備至,一時傳為佳話。

1964年,台灣世面上傳出了一本少帥幾年前寫的《
西安事變懺悔錄》,那是為了編纂少帥的在西安事變中的子虛烏有的罪行,找人代筆的。
她剛一看到這本書,斷定既不是張學良自己寫的,也不是趙四小姐寫的。
她毫不忌諱地說出自己的丈夫根本無法比肩書裡的文學水平,以前很多的文字也是秘書寫的。
而趙四小姐沒有在學校裡念過什麼書,
也從來沒有認真自修學習,如此文筆更不可能由她代勞。
那隻不過是特務策劃的,由趙四小姐代為認賬抄一抄罷了。

她對那些追逐漢卿的女子,總是輕敵,總是不屑的。
在她眼裡,那些女人只能靠與男人糾纏在一起,
靠愛情博得一世美名,而她不是。
她會像宋氏三姐妹那樣,靠自己的一身才學與見識,獨立於世。
她是得力助手與靈魂伴侶,絕非低頭順眉的附屬品。
她當然有輕敵的資本。
她是東北王張作霖欽定的兒媳。
父親與張作霖相識,相交很好便拜了把兄弟。
張作霖看她讀書很用功,常誇她是女秀才。
還親自給自己的大兒子張學良提親。
可是於鳳至的父母卻不同意,認為當官的都是三妻四妾,
女兒嫁過去後肯定受委屈,便拒絕了親事。
父母讓她自行決定。
沒想到張作霖竟然同意了這種說法,兩人結婚前,
他便把自己的大兒子張學良安排到村子裡住,
讓他與於鳳至相處,相熟,自由戀愛。
果然,張學良愛上了於鳳至,
他總是拉著她的手,保證永遠聽她的話,決不變心。
這時,她才點了頭。
而張作霖更決絕,為了他心愛的兒媳,
甚至不惜許諾:張學良永不納妾。

她還認了宋美齡的母親做乾媽,與宋美齡關係也非常好,
她的朋友圈比起趙四小姐來說,可是永遠夠不著的頂配。
而且所有的私交中,都不是出於利用,而是相互欣賞。
讀她的傳記,只得見一個女子的風度雅緻,
她受過的苦被一筆帶過,
她歷過的悲傷似乎不值一提,滿篇都是吶喊、高歌、求索。
讀來,或許以為是個十幾歲的少年郎
訴說自己理想不得實現的悲苦,
仔細一看卻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的夢魔。
她一生都在為少帥的自由而奔走呼籲,至死成書,流傳百世,
讓後人也見證這份淹沒在冰冷歷史中的熱血沸騰的真情。
沒有希望的執著最是磨人,而她卻硬生生磨了半輩子。

有一位老將軍曾說,
“ 張夫人在美國時,始終是用意志支持身體,
強撐著向前,並活到高齡。
這不是醫學奇蹟,是愛情,
中國婦女忠貞的愛情產生的奇蹟。 ”

是啊,她總是記得少帥的好。
生第四個孩子時,她大出血生命垂危。
家裡人擔心萬一出了意外,三個年幼的孩子無人照顧,
丈夫又沒了服待的人,就提出讓她的侄女嫁給少帥。
當時,少帥說,
“ 我現在娶別的女人過門不是催她早死嗎?
即使她真的不行了,也要她同意我才能答應。”
與當年新婚時一樣,也是要她同意了,事情才能走下一步。
後來她奇蹟般的痊癒了,便拼盡全力地對他好。
他被軟禁的消息傳來,她立即安排了子女在英國入學,自己趕回國內。
宋美齡與孔祥熙去接她,問她該如何安排。
她只說,
“ 漢卿身陷囚禁,所受打擊太大,
需要我的支持、勸解、安慰。幫他度過難關。 ”
她堅定地說,“他有不測,我當陪同赴黃泉為伴。”

少帥被軟禁的頭幾年,常常冒出自殺的念頭。
他與特務同一桌吃飯,休閒時就被寸步不離地看守。
白天強顏應付,晚上回到房間裡獨處一室時便流淚不已。
這些淒苦歲月裡,於鳳至一直陪伴在他身旁。
多少煎熬,她卻隻字未提。
他反復哼唱京戲《四郎探母》,
用戲詞來訴說自己喪失自由的痛楚:“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於鳳至聽了,心情抑鬱,淚流不止。
少帥便囑咐她說,
“ 記住,這是我的實況,問我的情況,這戲詞就是我的實況。 ”
她為他焦慮、痛苦,心情始終抑鬱。
再加上輾轉囚禁的地方一個比一個艱苦。
到了貴州時,氣候潮濕,生活待遇也越發惡劣,她病了。
在醫院檢查時,確診為乳腺癌。

張學良勸她出國治療,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來。
張學良告訴於鳳至:
如今的職責不僅僅是照顧囚禁中的漢卿了,
而是安排子女出國,保護好他們,
還要為他的自由向全世界呼籲,他根本沒有罪。
她答應離開,永不回來。
但她擔心他的安危,
她願意讓當時遠在香港的趙四小姐來照顧張學良。
宋美齡安排她出了國。
在醫院裡,
她接連經歷了數次化療和兩次大規模的胸外科手術,
頭髮掉光了
命換回來了,人也不完整了。
出國前,她要少帥答應她的,任何情況下決不自殺,
盡一切可能委曲求全地應付周遭,保全自己以求得到自由。
如今,這句話成了她活下去的座右銘。
此時此刻開始,她便得在不完整的身體上委曲求全,
便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境況中委曲求全。
於是,她學外語,學炒股,學著投資房地產,
學著去像一個單親母親那樣照顧子女的學習與生活,
而堅持這一切的動力,不過是她堅定地相信,
她是在打造與張學良重逢後的自由自在的美好未來。
她孜孜不倦的守候,堅定不移的等待,最後卻換來了一張離婚協議書。

前來送信的人解釋說,這是你鬧的,
政府對少帥這樣的管束已經很寬大了。
送信人更挑明了說,
“ 少帥經過多年教育,已經認罪和守法了。
願意與趙四小姐在台灣終老。你不懂的,趙四懂。
趙四小姐說少帥確實罪大,政府很恩典他了。 ”
她打電話過去,少帥在電話裡說,
“ 我們永遠是我們,這事由你決定如何應付,我還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
“我們永遠是我們”這句話對她來說無比重要,她又哭了。
因為怕他再受苦難,她匆匆簽了字。
可她卻從未承認兩人離了婚。

宋美齡與她每年都互寄聖誕和新年賀卡。
這年,她在信封上落筆的仍然是張夫人。
一直都是,每年依舊。
或許這是政治交往的手段,但她卻當做至寶寫進了回憶錄裡。
她看重的是愛的本身,只要少帥還在說“我們”,
還在唱《四郎探母》,她就知道即使沒了婚姻的捆綁,兩人仍舊是至親至愛的。
正是這份感情,讓她挺過了未來接二連三更多的打擊。

幾年後,她大出血那次所生的小兒子夭折了。
二戰中,二兒子精神失常,
在去往台灣尋找父親的路上病重,死於台灣精神病院。
本以為災禍的額度已經用完了,然而,在一次飆車中,
她最珍視也是唯一活著的大兒子因車禍成了植物人,不久便辭世。
她說,
“ 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漢卿啊!
我只有在看到孫女、孫子們成長時,才略感到一點安慰。 ”
她一轉之前的悲戚,堅定地說,
“漢卿的這一囑託(照顧子女),我辦到了!”
命運對她究竟公平過了沒?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她等待了一輩子的人,最終卻與別人廝守終生。
這是事實,但以下的幾句也是事實:
兩人一別後便永遠不見,從此丈夫心中的她永遠與現實中會變老,
在少帥的想像裡,她將永遠是肯為他出謀劃策的摯愛之人,
年輕貌美,穿著時髦,周身一襲貂皮大衣,
與他十指相扣穿越熱鬧大街、人潮人海。
從此,她再也不會讓他失望、厭惡。
記憶凍結了時間,為張學良飽受創傷的心靈寫下永誌難忘的一刻,
在未來,他記憶於鳳至的方式,
永遠是“我的夫人於鳳至因乳腺癌,去美國。”
他不會知道她受了多少苦,不會知道她內心有多煎熬,
她的美停留在記憶中,成了最驚豔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