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季的《歌手》如約而至,在這群大腕兒在中間,有幾張生面孔。
他們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但有幾首歌卻一定是讓你們如雷貫耳的,
比如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計劃,這是他們樂隊的名字,其實我們早已耳熟能詳。

站在湖南衛視斥巨資打造的,世界頂尖的舞台上,
逃跑計劃的成員們仍是穿著簡單的格子襯衫、牛仔服。
唱起歌來也是如以往無數次站在露天的音樂節舞台上一樣,簡單、隨性、卻又無比真摯。
第一輪競演過後,逃跑計劃排名墊了底,但他們自己卻一點都不在意。

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深知對手強悍,而是因為這十多年來一腔孤勇追的音樂之路,
其實已經足夠讓他們明白,什麼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名次?金牌?鮮花掌聲?
不,那些真正追夢而至的人,早已不把這些名利看在眼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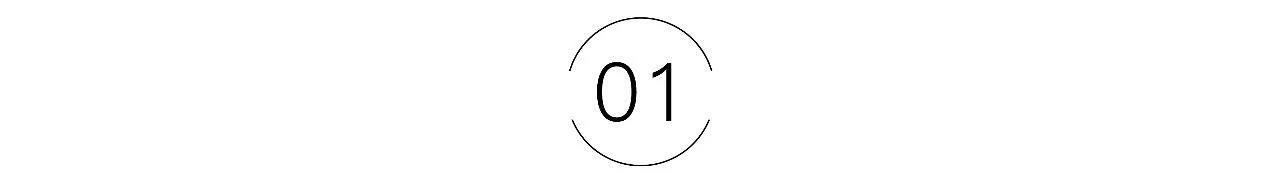
“大家剛剛知道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做音樂十年了。
從彈吉他開始,這十幾年每天都在想的一件事是,
找樂手,找樂隊,找排練室,買音響,買琴,
想了十幾年,終於想出一首作品,大家認可了。”
2014年張傑終於把《夜空中最亮的星》這首2011年就發表了的歌曲唱火了,
逃跑計劃也隨之出名。
而在此之前是他們幾個不得不咬著牙、互相支撐著才能熬過的十個春夏秋冬。

逃跑計劃這個樂隊,如果追根朔源,應該是從孔雀樂隊開始的,
或者更早一點,是從少年毛川得到了一張唐朝樂隊的專輯開始的。
因為唐朝,毛川愛上搖滾,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一頭扎進北京城,跑遍了北京的酒吧後,他拉上馬曉東組成了孔雀樂隊。
可那時候連飯都吃不飽,樂隊又怎麼能維持呢?
沒多久當時的另外兩位成員出走,樂隊解散了。

▲樂隊早期,毛川在排練室排練
毛川不甘心,繼續招兵買馬,直到2007年底,
鍵盤小田,鼓手張超,貝司手小剛加入樂隊,
他們幾個商量著把樂隊名字改成了“逃跑計劃”。
後來紅桃也入了夥兒,就這麼著,他們顫顫巍巍地重新出發了。
逃跑計劃第一次拿到演出費的時候,五個大小夥子,一個人只分到幾十塊錢,可他們高興極了:
“大家湊在一起,總算賺到第一筆錢了,可以賺錢了就說明這事兒能幹。”
一點點喜悅,一絲絲光亮就足以支撐他們走下去。

為了能登台表演他們什麼活兒都接,演出雖然多,
但當時可以分到的錢卻少的可憐,每個人也就幾十塊錢。
唱完歌一高興在路邊攤吃頓燒烤,連搭車回家的錢都沒了。
後來有了經紀人,每次演出完,大家在一起開會,在暢想未來的時候。
經紀人讓他們試想一下,如果以後出名了,每場演出每人能分2000塊錢,
眾人譁然,覺得這根本不可能。
那都已經是07年了,市面上多的是一場演出能拿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歌手。

2008年,他們終於因為一首《08年我們結婚》稍微有了點名氣,
開始接到各大音樂節的邀請,也籌備起自己的小巡演。
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又似乎其實一切都沒變。
2009年他們去南京巡演,演出結束後要坐凌晨的火車回去。
但是為了省200塊的賓館錢,幾個大男孩兒就生生在古堡酒吧旁的麥當勞坐了一晚上。
就這樣堅持著春去冬來,好的壞的都在發生,他們總算達成所願。

“10年前,我每天騎車在這條路上,每天去後海的酒吧唱歌,
我每天都能路過這裡。我從來不敢想我有一天能站在這裡開演唱會。”
2017年6月,逃跑計劃登上了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舞台。
那一天,工體幾萬個觀眾一同在黑暗中亮起手機燈光,
大聲的跟著他們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請照亮我前行”。
終於成名之後,他們身上多了一些責任感,毛川說:
“有時候,我們也會反過頭來想想,
也許在某一時刻你已經成為了一些人心目中的那個英雄,
就像十多年前我聽到搖滾樂時一樣。
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或者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人可能看到你,
你的一個行為或一首歌,也許就可以改變一個迷茫少年的人生;
逃跑計劃的成功或許可以給更多的地下樂隊以希望。
如果我們去這些地方做這些事情,可以給大家一點兒信心,這些還是值得的。”
十二年了,走過了幾個春夏秋冬,
這幾個留蘑菇頭的小夥子也已經變成了蓄著小鬍子,梳著背頭的男人。

經歷了那些堅持與努力,經歷了那些苦難與挫折,
經歷了哪些讚美與謾罵,世界在他們眼中反而變得更簡單了。
這時他們更願意唱一些溫柔的歌,給那些身處悲傷的人們帶去如陽光般的溫暖回憶。
就像第一場競演中他們所唱的《一萬次悲傷》。
就似乎在說:即使追夢路上有一萬次悲傷,也希望陽光能永遠照進我們的回憶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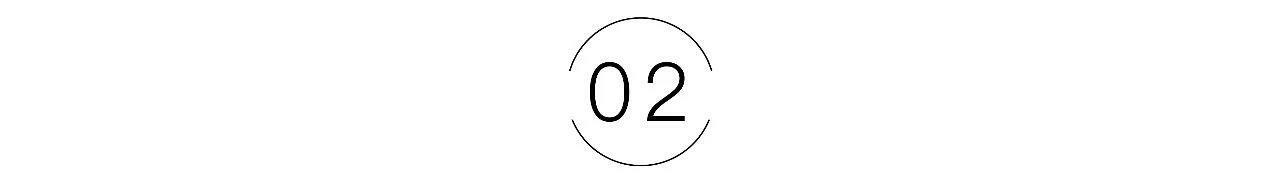
無名歌手紅了以後,總是避免不了由地下轉到地上。
然後利益牽扯的多了,身不由己的事也就多了,
隨之而來的就是各方的批評,首當其中便是最初那些呼天搶地要喜歡他們的人。
就像2013年毛川去參加《中國夢之聲》,還有後來整個逃跑計劃的走紅,
都讓一些歌迷“義憤填膺”,說他們變了,背叛搖滾了,不獨立不酷了。

▲參加《中國夢之聲》的毛川
李志也一樣,今年簽約了公司後,罵他的人太多了。
其實在近幾年裡,李志在很多人心裡已經不僅僅是一位歌手了,
他代表著那種浪漫的,熱烈的,精神至上的理想主義。
1999年退學後,他開始搞音樂,北上又南下,唱歌、創作、思考,
20出頭的時候,李志就是這麼活著。
後來他借錢做了張專輯《被禁忌的遊戲》,
這張專輯後來被人們反復誇讚,但在當時賣不出去不說,還得被人嘲笑。

▲《被禁忌的遊戲》專輯封面
2005年的《梵高先生》,2006年的《這個世界還會好麼》其實都是虧本,
虧的他欠了一屁股債,一度連飯都吃不上。
但虧著虧著,李志卻慢慢火了。
太多人問他是怎麼做的營銷,能把自己搞的這麼火,
李志莫名其妙,他從沒想過出名,但沒人信。
不過他也不在乎,仍是獨自一人,不簽公司也不上電視。
仍是穿著最便宜的衣服抱著把吉他在各種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唱歌,
歌聲伴著煙霧從口中吐出,音樂都沾上了尼古丁、聽得嗆人。

2014年李志自己開了公司,還是唱想唱的歌,說想說的話,懟想懟的人,
他也在這之後組了個團隊“參參肆”。
參參肆即334,也是李志的一個願望,他計劃用12年的時間,在全國334個地級市做巡演:
“2004年,我26歲,做了第一張小樣。
一轉眼12年過去了,一個小輪迴。
回頭想想,還算沒太過虛度韶華。
我想再用12年,在全國334個地級市做334場演出。
讓更多人聽到、看到、參與到現代音樂中來。”
就是為了這個願望,李志付出了特別多,時間、金錢、健康......

除此之外,李志還有個身份,著名的維權鬥士,只要侵他音樂版權的,
什麼大平台,什麼著名機構,他一概不怕,獨自一個人就敢迎頭而上。
也有人問他怎麼這麼勇敢,他似笑非笑:“沒辦法啊。”
那時候所有人都誇他,把他當成什麼理想主義的化身、正義的鬥士,
當成是自己想要成為卻不敢成為的那種人。

2018年10月23日,李志與太合音樂集團旗下的麥田音樂廠牌達成合作。
這個單打獨鬥了二十年的,不羈的,
從來都自由如風的歌手終於也沒能真的脫離利益紛雜的世界。
曾經那些口中宣揚著愛他的人,在這時候調轉了槍口,
痛訴他的背叛,譴責他的改變,也有人痛心疾首的表示不理解。
但這又有什麼理解不了的呢,他就是太疲憊了,自己一個人扛不住了。

其實在更早之前,李志就已力不從心。
艱難推行的“334計劃”,團隊裡幾十個人的收入,都是壓在他身上的責任。
當然最讓他難過的還是越年長越發現自己的音樂才華還達不到自己想去的高度。
李志希望自己能做個有價值的人,這一點是他早已融入骨血的理想,
不然他也不會在1999年退學。
如果音樂無法達到另一種高度去實現這個價值,那他就想用一些行動去達成。

理想、責任,他都掛在身上,日復一日年紀漸長,
40歲的李志壓咬牙堅持,卻總有撐不下去的時候。
這一條理想之路,旁人看到的是熱血,是酷。
但在他這裡應該是痛苦的,也是孤獨的。
可李志還是這樣走著,也許會妥協,也許會改變,
但最本質的那些理想,始終還在他的骨血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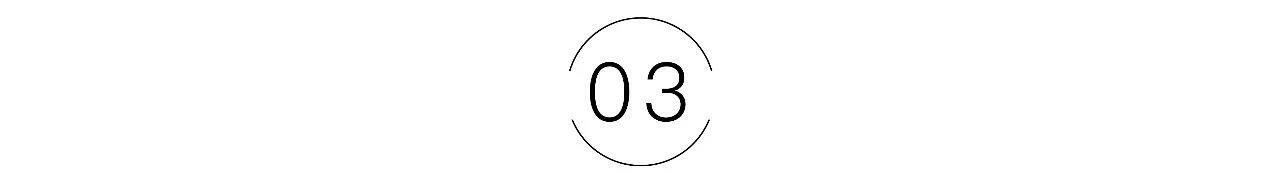
不過四十歲的李志也會有喪氣的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的這種堅持是否真的產生了影響,是否讓什麼人有所感觸。
張瑋瑋覺得他根本不用擔心這一點。
前一段時間張瑋瑋跟著李志和參參肆跑了幾個城市,
他一開始只是好奇,後來就有了震撼。
他說“參參肆計劃”特別像少年人在大學裡許下的熱血誓言,
但四十歲的李志真的做到了,並一直在做。

▲張瑋瑋
李志堅持的樣子一下又點燃了張瑋瑋,回到家後,
他不再那麼心安理得的沉溺在“瓶頸期”,又開始逼著自己創作。
張瑋瑋是“野孩子樂隊”的成員,“野孩子”這個樂從1995年小索和張栓組它開始,
聚散離合,到如今已是第二十四個年頭。
1996年,小索和張佺從延安出發,沿黃河步行至內蒙。
一路上,他們采風、創作,就這樣給樂隊打下了民歌基礎。
到了北京後,加入新成員,但樂隊的人來了又走,其實固定的時候不多。

▲野孩子樂隊早期成員
不過後來張瑋瑋總是提起當初在北京的時光,
提起他們像朝九晚五上班一樣的每日排練,提起他們艱苦又發自內心踏實的歲月。
2001年,野孩子樂隊在北京創辦“河”酒吧,寸土寸金的三裡屯南街上。

▲河酒吧
左小祖咒、萬曉利、周雲蓬、王娟......等等音樂人,
都在那裡起步,都在那裡將初心妥帖安置,他們有了自己的烏托邦。
那樣的日子應當是異常美好的,所以才讓他們許下這樣的願望:
“我們這輩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後一起到法國找一個小鎮,
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這麼些人,誰都喜歡,就一輩子待在一起。”
2003年,理想撐不住現實,河酒吧轉讓,烏托邦倒塌,
一年後樂隊最初的創始人之一小索也因病辭世。
音樂人再次隨風飄搖,野孩子解散。

張栓去了大理,樂隊剩下的幾人也四散在各處,幾年的漂泊,
他們撐得過無定的生活,卻始終抵不過孤獨。
後來張瑋瑋和郭龍也搬去了大理,野孩子又重組了,
2014年樂隊又加入吉他手馬雪松和鼓手武銳形成固定班底。
歌又唱了起來,從雲南繞到北京,最後還是流入家鄉的那條黃河。

▲野孩子樂隊成員在小索墓前合影
二十四年的歲月,幾多離別,幾多重生,野孩子們默默唱著歌。
不管有沒有人聽,不管站在哪裡,不管誰說了什麼,他們總是默默唱著歌。
唱著唱著,人都老了。
唱著唱著,他們還似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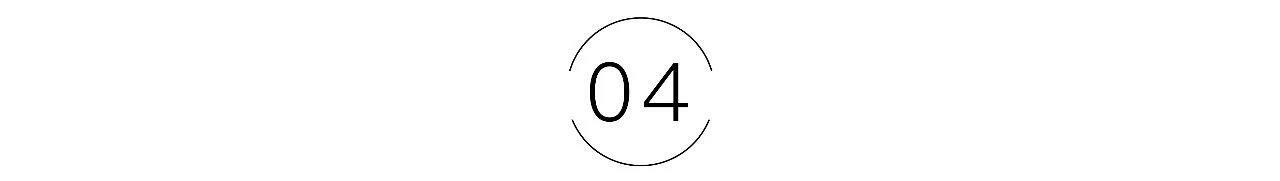
野孩子樂隊的成員現在大多定居大理。
2013年張瑋瑋著急在大理租下一個二層小樓的時候,
萬曉利也離開居住多年的北京,把家搬到了杭州。
萬曉利到北京的時間和野孩子差不多,1995年前後,
他多次往返於北京和邯鄲之間,就是為了把手裡的二十幾首歌換成一張唱片。

其實他那時候已經結婚了,工作在一個酒廠,每個月不到200塊錢,也算不錯了。
可他就想唱歌,誰也攔不住。
但這事兒一直沒成,沒有公司願意出錢。
1997年萬曉利又一次來北京,這次他沒走,租了房子,找到酒吧唱歌,
2001年野孩子的河酒吧開業,萬曉利搭檔小河,每週三都去那兒演出。
烏托邦裡的每個人都是高興的。

2002年對萬曉利來說是不一樣的,他與Badhead簽了約,
錄了第一張專輯《走過來走過去》,還在天通苑買了房。
後來萬曉利買了電腦,從頭開始學習,然後用電腦編、學英文然後自己編曲。
那段時按沉迷創作的萬曉利其實有點揭不開鍋的徵兆,
但他還是覺得“太美了”,一直做音樂“太美了”。
2006年,老狼聽了萬曉利自己錄的新專輯《這一切沒有想像的那麼糟》,
頓覺驚艷,將萬曉利推薦給獨立廠牌“十三月”,並發行了這張專輯。

▲老狼和萬曉利
這之後萬曉利第一次嚐到成名的滋味,他不習慣,也不喜歡。
後來萬曉利也辦了演唱會,有了粉絲,再後來民謠漸漸火了,老朋友、小後輩都出了名。
2014年,韓寒把他翻唱的《女兒情》作為電影插曲;
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裡翻唱了他的《陀螺》。
更多人知道了有個瘦瘦的民謠老歌手叫萬曉利,但萬曉利一言不發。

17年南方周末採訪萬曉利,他說了一句:
“我沒有想過。外部的這些還是想得比較少,音樂已經......音樂已經夠我受的了。”
他把那些其實輕而易舉就可以贏得的名利推出門外,
獨自一人抱著吉他彈著琴,他思考、創作、他沉迷在音樂裡,飽受折磨也甘之如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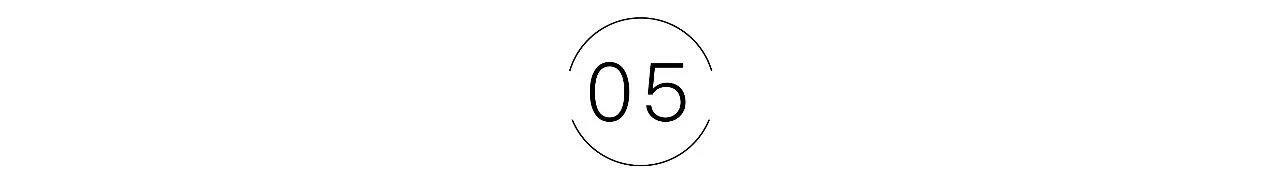
上述的這幾位,說小眾,也不算小眾,畢竟唱了這麼多年歌,總有認識他們的。
但也絕對稱不上個大眾,走到路上,能認出他們的其實真的也沒幾個。
不過他們作品的知名度正與他們本人成反比。

《米店》,不僅被很多大咖翻唱,還被羅永浩翻牌,
他把這首歌編輯成鈴聲,預置到他所有在售的手機裡。
世道千變萬化、潮流轉瞬即逝,那些個金光閃閃的舞台上,站上去的人總是不重複。
但總也有一些人,他們年輕時追夢而來,見證過苦難,撕扯過自己。
他們從小角落裡起航,以至於後來他們總是與金碧輝煌的舞台格格不入,

歌總在那裡,歌永遠在那裡。那歌與人跨過山海與歲月,還是走到了現在。
李志用那首歌問過一句:這個世界會好嗎?
我想還是會好的吧,哪怕千變萬化,哪怕面目全非,也總有像他們這樣的追夢者。
就像一隻只螢火蟲,用自己的力量散發著微小的光和熱。
似乎微不足道,但連在一起也亮如白晝。
這個世界一定會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