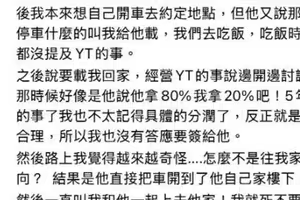10年前遇見的吐瓦魯女生Senny,當年曾一起出海。
10年前,我曾赴「世界第四小的國家」吐瓦魯。相隔10年的時間,任何國家和旅遊目的地都是會變的。吐瓦魯臨赤道,常年天氣炙熱,空氣裡有海的濕氣。機場旁邊的小旅館,走路20步就是大海。回想10年前的台灣,正進入WIFI時代、人人都有手機,大夥熱烈的開始使用Facebook。吐瓦魯呢?只有一間鐵皮屋的網咖,撥接上網。
機場旁的小旅館,已是當年吐瓦魯最宜人的旅店。短居數日,在旅館用非常涓細的冷水淋浴時,被櫃台硬生生把水關掉,「你怎麼可以用那麼多水洗澡啦?」我頂著充滿泡沫的頭髮、包裹毛巾衝出浴室時,旅館女主人站在大廳對我大吼。那年的吐瓦魯,旅店房間均無冷氣,只有老舊的電風扇支撐。覺得好熱,熱就跳下海,海水是在地人的生活用水。

許多人在吐瓦魯瀉湖邊玩水,如今這個地方已經填海造地,不復存在。
那年我在小旅館裡認識了一名員工,也是當地女孩Senny,25歲的她,丈夫是船員,一年僅回國一次,她獨自撫養母親與2名孩子,簡居在離海2米的一間鐵皮屋裡。每當吐瓦魯大潮時節,海水漫上陸地,會直接打入她的房子。
Senny曾騎機車帶我走逛過吐瓦魯,我們包了船航行到外島。她與朋友上樹採了椰子給我當飲用水喝。閒來無事的某日,我們坐在沙灘上,Senny開口問我:「你的父母還活著嗎?」奇特的問候讓人嚇了一跳,我說是的,怎麼了嗎?她問我能否為她和母親拍張照,「這樣等我媽媽過世,就有照片可以看了。」她哈哈大笑,語調輕鬆的這樣回答。

10年前Senny抱著孩子與媽媽,曾要求我拍下這張照片。
10年前離開吐瓦魯那天,我在機場旁的旅館整理行李,「我相信我們還會再見面的,等你下次回吐瓦魯。」她反覆這樣說,我心中知道,那麼遙遠的島國,離開一趟怎麼可能有機會再回來?我倆各自留下Email,卻很快的完全失去聯繫。

回訪吐瓦魯這天,機場跑道出現了完整的彩虹。
相隔10年,我竟然又有機會踏上這座極為偏遠的島嶼。吐瓦魯卻也發生很多改變。機場旁的小旅館已經不是島上最好的私人旅店了,島上多了幾間中餐廳,海濱填海造了地,蓋了幾棟新建築。吐瓦魯已經有網路了,只是非常慢、價格高昂,仍很難與人聯繫上。我想起記憶中的Senny,想找她卻不知道該從何找起。
回到機場旁的旅館,旅館早已經不是島上最佳選擇了。到訪這天沒有任何旅客,旅館員工的面孔也全換了,旅館主人思考了許久,好不容易幫我拼出Senny的吐瓦魯名字Sennymita,她手指島嶼另一端,跟我說,應該到另一頭,「她家應該在那邊的某一個便利商店那邊。」
我跟攝影騎車在島嶼尋人,吐瓦魯建築無地址可循,問了警察商店位置,他們也是隨手一指,我們在島上四處尋找相似建築,想找到她家,感覺像大海撈針。此時突然靈光一閃,吐瓦魯人口極少,也許問問路人還有可能知道。

機場上這家人認識Senny,她們協助我找到她家。
「你認識Sennymita嗎?」機場跑道上有一家人坐在車上等著看球賽,我隨口一問,「喔!你要找她嗎?她家在那一邊。」什麼?她竟然認識Senny,我趕忙掏出手機中的照片給她看,「對!她跟我同年,我們是同學啦!」
她說順著路直直走,過了3個小路口再問,Senny家就在那附近。我們在騎上車,「Sennymita在這裡嗎?」一名坐在屋前的女士回答我:「對啊,你往後走就是她家。不過她去紐西蘭了。」
心中似乎早已經猜到結果,相隔7,000公裡能再回來,找到10年不見的朋友,果然是不容易的事。我往海的方向走,一邊大喊:「Sennymita家在這邊嗎?」有名男子回應我:「對啊!在這裡!」他站起來向我揮手。

Senny先生與我的合照,他如今長居吐瓦魯照顧孩子。
「你好,我是Senny的朋友…」,「我知道,2009年在Filamona Hotel對吧?我知道你喔。」真的假的啦?都已經整整10年了,「我是Senny的先生,我有聽她說過,她還記得你喔。」
只是Senny如今已不在吐瓦魯,她在紐西蘭工廠工作,一年回家一次。吐瓦魯政府鼓勵居民赴海外生活工作,因為島上資源少,工作機會自然也極少,Senny的丈夫、孩子仍在吐瓦魯,她獨自遠赴異鄉掙錢養家。
問起Senny,母親還好嗎?Senny丈夫指了腳下,「她媽媽走了,就在這裡。」他充滿笑容這樣說道。腳下是一層薄土,立了小小如墓碑般的牌子,我們就站在這塊土地上頭。

10年前我與Senny到海邊,舊碼頭邊,孩子們下海玩水,希望他們一直保有這樣的單純快樂。
很多人說,吐瓦魯人的思念特別長,因為這座島嶼擁有最豐盛的資源,是每日浪淘起伏的聲音。島上一切極簡,能分散注意力的事物也少,這兒是世界最單純的角落。相隔10年,再踏上吐瓦魯,我竟見證了這樣的思念。
回到台灣,跟Senny聯繫上,她傳了許多她在異鄉的照片給我,「希望有一天,等你回到吐瓦魯再見面。」她又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