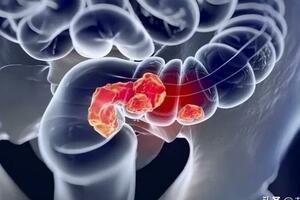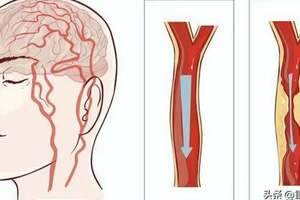爺爺躺在病榻上獨自掙扎,家人宣稱“死亡對他是一種解脫”。原來我們從未學過該如何告別
原創 三聯生活周刊 2019-07-08 19:42:00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3期“個人問題”欄目,原文標題《沒學會好好告別的人》
文/一術

在離89周歲生日兩天的時候,爺爺走了。我本來以為我對這件事能夠很超然地接受,一是因為我已經做了長久的心理准備;二是大半年前他半夜從床上摔到地上,其後每天只能在輪椅和床上度日,大小便無法自理,除了吃飯,只能呆坐、睡覺。我和弟弟討論過許多次,覺得他的生命已經進入純粹的無意義和痛苦狀態,死亡對他來說或許是種解脫。
但那時候我們並未真正地正視過死亡本身。離世前的這一年,爺爺一直生活在偏僻的老家小鎮,由同樣年邁的奶奶和輪流回家侍奉的子女照顧。2018年12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家裡突然打電話來,說爺爺不再進食,身上出現大面積的青紫色和鼓包,第二天送去縣醫院,檢查結論是內髒器官衰竭,嚴重內出血,挽救餘地不大,爺爺當天就被帶回家裡。
我和弟弟是在第三天中午到家的,隨後,伯父、爸爸和幾個姑姑也從各地回來等候送終。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爺爺的大部分子女孫輩都在縣城或者更遠的外地工作,如果不是他真正要臨終了,已經很難真的有什麼事可以再把大家全部聚在一起。大家一致默認只需要他自己的6個子女回家守候,兒媳、女婿和孫輩則只需要回家參加葬禮,因為臨終之前這段日子無法准確預料,有些耗不起的意味。
在爺爺之前,我的外公外婆分別在我讀初中二年級和高中三年級時就去世了,我沒有參加他們的葬禮。因為家長和老師們一致認為,對當時的我來說,學習更重要,我也服從了這個決定,因為這個,初中的數學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公開表揚過我。我當時恨不得找個洞鑽進去,但要很多年過後,我才真正確切地知道我到底失去了什麼。
在工作中,我接觸過很多的生老病死,但親眼見證死亡的陰翳一寸一寸無法阻擋地覆蓋而來,我也是第一次。10月份回家過一趟,當時爺爺已經十分消瘦,但尚且是普通范圍內的消瘦,但這一次不是了。他每日黑便,那是消化系統出血的證明,他無法再從外界汲取能量了,肌肉和脂肪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流失,直到全身每根骨頭變得清晰可見。他的力氣弱到無法自主翻身,無法咳嗽,無法向我們示意他又大小便了,意識模糊到無法吐出一個清晰的詞語。
但只有他一個人在艱苦掙扎,回來的兒女們每天熱熱鬧鬧地做飯、聚餐,商量後事,猜測他到底會在哪一刻離世,甚至還嚴肅討論過他的生辰八字,好測算如果他在哪一刻離世是不吉利的。他們有時候到床跟前看一眼,說“他還挺安穩的”。不需要再給他准備飯菜了,因為在病情突然加重的那兩天,他連水都是會吐的,他們統一對外宣稱,他已茶飯不進。
然而,如果仔細觀察,並不是那樣的。在過了病情轉變的那兩天之後,他似乎依然無法吸收,但變得極渴極餓,有一次甚至拽住我給他喂水的勺子往嘴子塞,突然之間力氣大到我都搶不過,我掰他的手指,他彷彿突然間明白,頹然地放開了,我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理解到的是什麼。另外一些時候,尤其是到了深夜,他變得極度痛苦而不安,不斷張嘴做出喊叫的樣子,卻發不出任何聲音,這種掙扎有時候會持續一兩個小時,有時候會持續大半個晚上,但他的掙扎是無聲的,所有人都默認他在安穩睡覺。
他全身幾乎只剩下骨架,但雙手卻是浮腫的,且冰冷。如果有一隻手伸給他,他會緊緊握住,往胸前拉;如果沒有手遞給他,他就一直在床沿和枕頭邊亂摸亂抓,伯父抱怨說這是被我和弟弟慣出的毛病。我提議過給他打止痛針或用吸痰器,但都被不容置疑地否決了。伯父、堂哥和堂姐分別是鎮醫院和縣城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他們更有醫學權威,我也很快選擇了不去破壞某種“和諧”。除了靜靜地坐在他身邊,握著他的手,實際上我也沒有真的做出任何能夠幫助他的事情。
最後的局面變成了,他獨自躺在床上沉默地掙扎,如同身在另一個星球,而其他人在隔壁房間烤火、閒聊,不再做出任何努力和關懷,一心一意等候最後時刻,並且宣稱“死亡對他是種解脫”。沒人認為這有何錯,街坊鄰居稱贊我們算得上孝順,至少都回家了。這個過程持續了漫長的7天,他的鼻息變得越來越弱,力氣變得越來越小。在那幾個看著他無聲嘶吼的深夜,我獨自坐在那裡,恐懼得渾身戰栗,生平第一次知道,死亡是一場如此漫長而痛苦的煎熬。而如果我們連看都不去看他的痛苦,又如何有資格替他說出“解脫”這個詞?
我能理解我的父輩,他們也未曾被好好對待過。因為人多,伯父的床鋪在堂屋,他睡覺時,大家一樣開著燈看電視,大聲交談,他從未覺得不妥。他們的消極和冷淡裡,有常年忍受的成分,有羞於表達的成分,也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即使活了幾十年,他們也未曾真正正視過死亡,更從未學過如何好好告別。